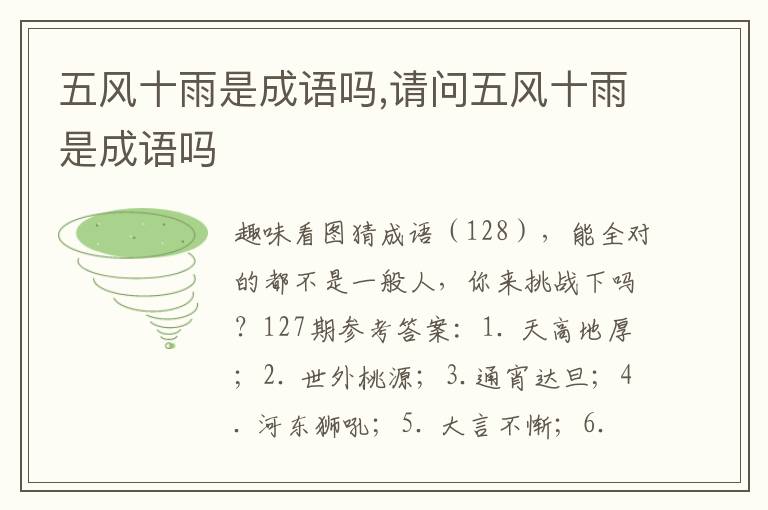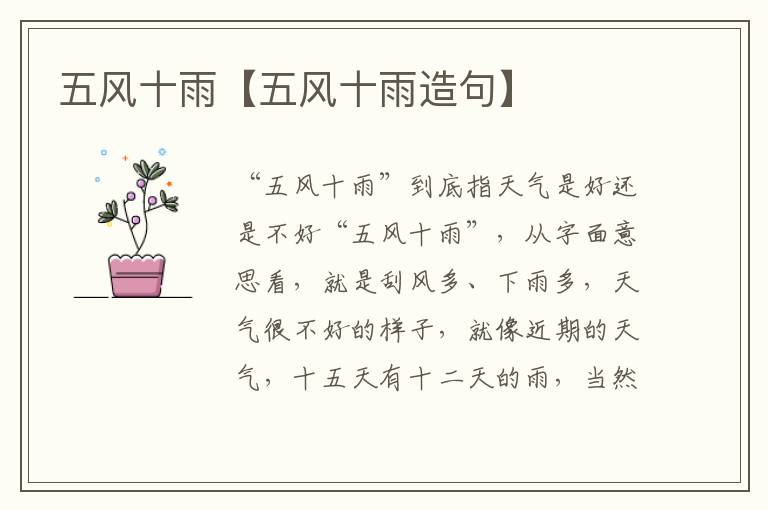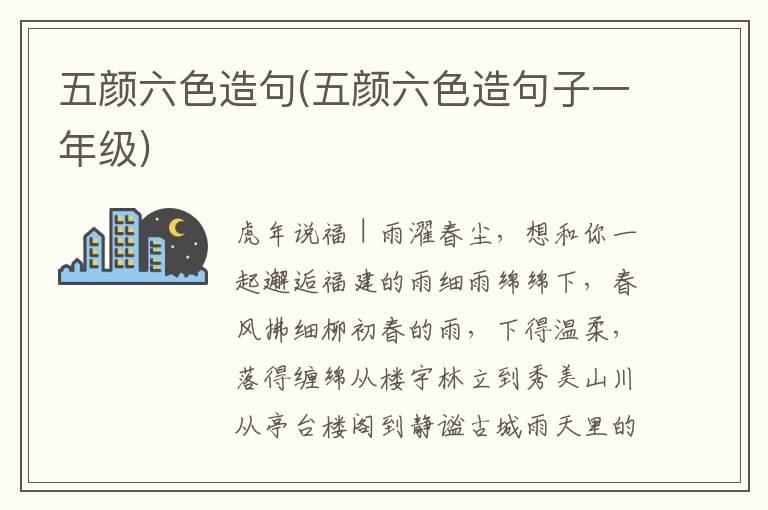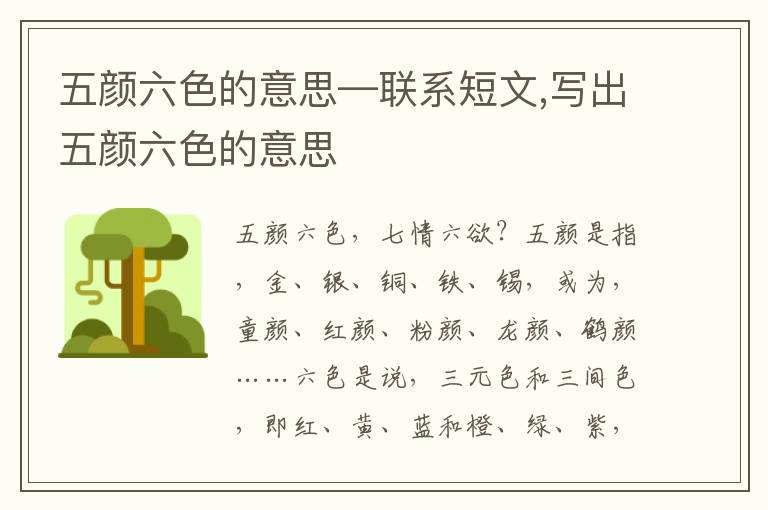从大山深处走出的文化世家
2020年11月末,我前往江西省修水县,参加修水县承办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因为,原本应在去年的这次会议延期到今年,又从上半年改在下半年,主题自然也由纪念陈寅恪逝世50周年改为纪念其诞辰130周年。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世家
算起来这是我第三次到修水了。第一次是在20世纪末,当时从县城到陈家大屋尚无可通机动车的道路,我和当地的一位朋友是在乘坐一段汽车后又在山林中步行了两个小时才来到位于崇山峻岭中的竹塅——也就是陈氏家族的所在地,那所著名的陈家大屋就静静地坐落在一座小山脚下,周围有小溪流过。那一刻的感动我至今记忆犹新,这里是陈宝箴、陈三立的故居,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文化世家的出发地。
陈家大屋外貌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应陈氏后人的热情挽留,我们还在陈家大屋住了一夜,并品尝了陈家后人为招待贵宾才会做的当地美食修水哨子,它用芋头和红薯粉为皮,包着以虾米、腊肉、油豆腐和笋干做的馅,蒸熟后上桌,香味扑鼻。后来也几次吃过哨子,总感觉没有那第一次的味道鲜美。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听陈家后人讲述当年陈家人在此艰难创业的故事,那场景是我一生难忘的体验。如今这自然已不可能——陈家大屋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连住在里面的当地农民早都搬迁出来,更不允许游客在里面过夜。
游客在陈家大屋外合影。作者供图
记得在返回修水县城时,我们决定步行,选择了一条比较近却极为坎坷的山路,据朋友说当年陈寅恪的祖辈如果要去县城,很可能就走的是这样的山路。我至今记得走那山路的艰险,因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要靠朋友用手里的竹竿拨开密密的草丛,顺便吓跑可能藏在里面的毒蛇,当时正是盛夏,我们走不多远就已大汗淋淋,随身携带的一瓶水很快就被喝完。也就在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个家族走出深山的艰难。作为客家人,陈氏家族依靠他们的辛勤和智慧,由一个棚户之家到耕读之家,再由耕读之家到仕宦之家,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世家。陈家数代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无法衡量,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中国农民的梦想,只是能够让梦想变为现实者少之又少。
图为陈寅恪夫妇和三个女儿的合影。新华社资料片
第二次去修水,则是应修水县的邀请,为他们修建陈寅恪纪念馆及维修陈家大屋等事提一些建议,当时去陈家大屋的路已经可以勉强让小汽车通过,但陈家大屋依然破破烂烂,如何尽快修复已经迫在眉睫。由于当时还不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修水又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资金筹集方面很有困难。不过当地还是表示,他们为陈寅恪及其家族生活成长在修水而自豪,而另一位值得他们自豪的是同样出身修水的宋代大文豪黄庭坚。不管多么困难,他们一定要把陈家大屋保护好,让更多人走进和了解陈寅恪家族——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文化世家。
陈家大屋。作者供图
这一次,是我第三次来到修水,明显感觉到当地人对我们的热情,以及他们在提及陈宝箴、陈三立和陈寅恪等名字时的自豪。他们对陈氏家族所表现出的敬佩和热爱,显然发自内心。会议之余,主办者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到陈家大屋参观考察,我惊喜地发现如今从县城到陈家大屋已经有一条宽敞的沥青公路,乘车仅需半个小时就可到达。不但陈家大屋早已得到维修,还新建了一些纪念性场馆以及接待游客的设施。这些维修和新建设施整体而言没有影响原来的地理风貌和文物原貌,在对房屋等建筑进行修缮时也注意到了修旧如旧,尽量保持原貌。从各位专家学者的反应看,他们对当地为陈家大屋及有关文物所做的保护工作是满意的,也都为当地农民所表现出的热情而感动。
2014年,大屋看护者的欧阳国泰打扫陈家大屋主厅。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在返回县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一直在激励陈家数代人一定要读书识字,一定要走出大山?仅仅是为了光宗耀祖?显然不是。我想到了陈家大屋门外空地上那两对有名的举人旗杆石和进士礅——一对是因陈宝箴中举而设,一对是因陈三立中进士而设。它们的出现不仅标志着陈家的出人头地,更是陈家成功走出大山的象征。后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湖南实行的新政,不仅有力呼应了维新变法,更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重要篇章。而陈氏父子之所以如此,正是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源于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不愿祖国走向衰落乃至被列强瓜分的悲惨结局。他们一定要走出大山,就是为了获得一个救国救民的机会,就是要实现“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中国文人一直坚持的理想。
重温陈寅恪对中西文化关系的阐释
所以陈寅恪才会10几岁就走出国门,然后海外留学20余年,广泛研究和了解西方文化却没有获得一个学位,因为他留学的目的不是镀金,而是寻找让中国文化重现辉煌的方法或途径。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强行进入和步步紧逼,传统文化陷入日趋衰落的境地,中国社会也因此遭受一次次动荡以及外敌入侵。“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困境”,就成为自龚自珍以来无数文人志士努力思考、探索的问题。
陈寅恪生前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大致而言,一个多世纪来国人对于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条路径。前者以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主张适当向外国学习,以渐进方式、维新变法;后者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主张全盘引进外来文化,以激进乃至手段批判和摧毁一切传统文化。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判定孰是孰非,而且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一味闭关锁国当然不行,而门户洞开、全面西化也非正确的途径。也许从根本上而言,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并大胆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最终形成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才能让中国文化焕发生机,并有可能重现辉煌。
陈寅恪、胡适和鲁迅等一代文化大师,他们都曾长期留学海外,对西方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他们也都有极为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尽管胡适、鲁迅等人在五四新文化时期也曾提出一些主张全面西化的过激口号,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与保守派斗争的策略,在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态度上他们的认识其实大同小异。诚如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说言: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不仅钱穆如此,再早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和郭嵩焘等人,也都明白当时的中国所面临之局面,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必须也只能对外开放,而且大门已经在洋枪洋炮的逼迫下被打开。所以曾国藩才会激赏俞樾的一句诗:花落春常在。只要中国文化这棵大树的本根不死,尽管有花落之时,但他们相信春天还会再来。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倡导的文化自信?而且他们的自信绝不是虚无缥缈的自高自大,而是建立在对中外文化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据此,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迄今依然有价值的处理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方法和途径,诸如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陈寅恪的“旧酒装新瓶”“取珠还椟”以及鲁迅的“拿来主义”,等等。在这里我们只简单谈一下陈寅恪的观点。
1961年吴宓自重庆到广州看望陈寅恪,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可见对“中体西用”之说陈寅恪一直持赞同态度,但他只是借用这一术语表明自己对如何接受外来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即应以我为主、外来文化应当为我所用,也即吴宓在上述一段引文后所加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寅恪认为,当佛教传入中土时由于中国文化已发展至相当高度,故佛教只有被改造才能适应中国社会之特性。因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正统地位,所以佛教为求立足,就极力谋求用儒家学说阐释内典,证明二者有相通相同乃至可以相互补充之处。但唐初僧徒一味袭用儒家,其佛教真义反而迷失。至新禅宗出现,才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繁琐章句之弊。韩愈受其影响,才有效禅宗之举直指华夏之特性。韩愈发现,《小戴记》中《大学》一篇,其思想内容非常适合用来重新阐释儒家思想及佛教学说,因为此篇对内讲谈心说性,对外讲济世安民,既合乎佛教意旨,也符合儒家理想,既以佛教思想修心养性,又以儒家思想济世安民,这就是所谓“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意旨所在。陈寅恪认为,韩愈正是受到新禅宗的影响,才奠定了后来宋代新儒学的基础。
在陈寅恪看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坚持以我为主,所谓“体”有主体、基础、主干之义;而所谓“用”则既有实际之用途,同时也有抽象之用,即可以用来对“中学”主体进行改造,禅宗的产生与流传即为一例。张之洞等早期“中体西用”论者认为“中学为体”这一点不可改变,西学只有实用价值,不能进入中学主体内部,显然陈寅恪的认识早已超越他们。
但陈寅恪为何依然采用“中体西用”这一说法呢?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他不满于当时成为主流的以西学为坐标而非参照系的观点(此可能是在暗批胡适);第二他认为“中体西用”说虽容易产生误解,但在无更好的术语之前仍不失为解释中外文化交流原则的较好说法。而且,对“中体西用”说固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自然说明概念的不严密性,但也表明它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阐释空间,从而可以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这一概念提出至今已一个多世纪,但人们对它依然兴趣不减。
由此在涉及现实问题时,陈寅恪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方法和方式。首先,对于外来文化,陈寅恪指出不外有两种引进方式:直接引进与间接引进。对此陈寅恪进行了分析:“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他认为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关键在于确定该文化是否对本民族文化有益,倘如此则必须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而通达其语言是前提。至于引进方式,倘对外来文化有清楚理解,则直接间接均无妨,问题在于以往的引进往往错把其不良部分误作精华,以至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陈寅恪特地点出日本、美国两处,而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思想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国家间接引进的,早期如梁启超、孙中山等,晚期如胡适等均为代表性人物,陈寅恪对他们的不满显而易见。
陈寅恪。
在他看来,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必须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所引进的是不是“原装”的?第二,即使是“原装”的、还没有丧失本来精意,但是否对中国文化之改造有益?第三,即使有益在引进时是否也需要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之特殊国情,以及如何改造?第四,其改造之后的结局如何?陈寅恪认为所有外来文化无论在其本土多么优良和有影响,在输入中国后都应有所改造以适应中国文化,事实上也都是如此:
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
陈寅恪认为,中体西用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原则是不可变的,但在具体交流过程中,如何善于引进精华、拒绝糟粕,如何进行加工改造以及怎样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融合,这仍然需要认真考虑。针对当时人们提出的“旧瓶装新酒”说,他提出了自己的“旧酒装新瓶”说。所谓瓶与酒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比喻,它们之间实质上属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一些正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文化正如一只古老的酒瓶,既可装“旧酒”,也可装“新酒”。如果说过去是“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在西方文化大举进入时则可“以不变应万变”,这“不变”的就是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倘若不得不变时,也要以渐变代速变,以少变代多变,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本立场。
然而倘若具体到把中外文化分别归之于瓶与酒,而认为酒可变而瓶不可换的话,则显然是片面之见。那么陈寅恪所谓的“新瓶旧酒”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提出“新瓶装旧酒”的: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人莫肯酤,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从上述引文可知,陈寅恪的“旧酒装新瓶”之说是直接承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而来。换言之,他认为“中体西用”虽不错,但在新形势下,有必要为传统之酒制造新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才得到他的肯定。中国固有的制度风俗、三纲五常等是“旧酒”,而宋明儒学在吸收佛教后编织的新义理系统是“新瓶”,陈寅恪认为这一“新瓶”制作得不错,使中国文化得以成功地又延续数百年。现在冯友兰在建立“新理学”体系时,声称要对旧理学“接着讲”,也即依然要像宋明儒学一样,在新时代条件下再次制造新瓶,这当然会受到陈寅恪的赞许。
其次,陈寅恪又提出了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具体方法:“避名具实、取珠还椟”。这与他后来所说的“旧酒新瓶”相呼应相补充,更可看出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取珠还椟”这一比喻显然也是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过一般专指外来文化,这也是对“中体西用”说的引申与发展。陈寅恪强调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而拒绝那些华而不实、不合中国国情的成分。
当然,具体操作起来并不容易。首先,判定何为珠、何为椟就相当有难度,彼时彼地为珠者,此时此地则未必。何况椟本身虽华而不实,毕竟还有一点形式美的价值,而在特定情势下,形式之引进也可能成为第一需要。那么,标准就只能是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以我之需要与否为是非。如果我们将“取珠还椟”和“新瓶旧酒”结合起来看,就会理解陈寅恪的深刻所在,特别是联系到陈寅恪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不为时代潮流所动,能从本质上把握中外文化的见解,的确深刻。
当陈寅恪提出“取珠还椟”时,正是五四时期;当他提出“新瓶旧酒”时,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真正提出有价值的思想并足以对抗“全盘西化”论者是代表新传统主义的新儒家。虽然新儒家也强调要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但他们心目中的“本位”有一个具体的内涵,即传统的道德规范及其内在的哲学精神。而且新儒家在论证传统文化有继续延续的必要性时,能够站在历史与哲学的高度,以人类发展和文化演变的普遍规律来论证继承传统的合理性,强调继承传统不是仅为了延续传统,而是为了重建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精神。所以他们当中如冯友兰就提出对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显然他们的用意就在于要在现代社会中重新阐释并建立新的文化规范,而其内涵与精神是承接传统文化的,也即为传统文化之“旧酒”制造一个恰当的“新瓶”。对此陈寅恪非常赞同,才欣然把自己的“旧酒”注入冯友兰的“新瓶”,希望冯友兰等人的尝试能够成功。
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和吊诡,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伴随着全球化的退潮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重新兴起,对传统文化给予充分重视并对其进行富有创造性的转化,已经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这个意义上,重温陈寅恪等一代文化大师对中西文化关系的阐释,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赵梅阳:陈寅恪「1890」——不古不今(2021年9月22日)
《赵梅阳:陈寅恪【1890】——不古不今》此文收录于赵梅阳《路遥知马力——开启感悟之门》总文集-第九十九子文集《登高壮观天地间》中。
时间:2021年9月22日……以此送给我那遥遥无期的奋斗征程……
不古不今
贵族世家袭,
史中求史识。
一生凄负气,
唐筼未分离。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2018年7月14日,赵梅阳摄影
诗致恩师——我虽平凡(十六首)(2021年9月10日整理)
诗致智库——鸾翔凤集(八首)(2021年9月11日整理)
诗致艺术——大师之道(十二首)(2021年9月12日整理)
诗致家人——心有灵犀(十首)(2021年9月13日整理)
诗致孩儿——如履薄冰(五十首)(2021年9月14日整理)
诗致朋友——天涯海角(二十四首)(2021年9月15日整理)
诗致生活——苦中作乐(三十二首)(2021年9月16日整理)
诗致青春——海阔天空(三十二首)(2021年9月17日整理)
诗致大师——画写授缘(一一六首)(2021年9月18日整理)
诗致端午——一路象北(八首)(2021年9月19日整理)
【声明】除有特别标注外,本文(及/或插图、配乐、摄影及摄像作品)之著作权由赵梅阳所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任何刊物、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链接、转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发表或发布。
[Statement] Except when specified, allrights of this article (including illustrations, soundtracks, photography andvideo works, etc) are reserved by the authors, Zhao Meiyang. No journal, media,website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reproduce, link, repost or in any otherforms publish the work without permission.
“不古不今”,啥意思?
陈寅恪说话、写文章、作诗很隐晦,给读他著作、诗文的人以很大相信空间,所以很多陈寅恪的研究专家、学者在他的著名学术断语上琢磨、猜测、考证,以求得自己的正解。这个“不古不今”的专用语句就是如此。
史学大师、江西修水人陈寅恪(1890~1969)
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陈本人没有说明,以至后来学者的解释很不一致。有人说陈所指的是他所专长、专攻的魏晋隋唐这一历史时期的学问,有人说是指中古时期,而更有人说,陈寅恪的“不古不今”是指的不是古文经学,也不是今文经学,而是晚清民国初期的经今古文之争的一段学人恩怨与学术公案。这些说法,显然没有说中要点。前两说可以判定为皮相之论,可姑置不提;而所谓的“不古不今”为晚清民国初期的经今古文之争的一段学人恩怨与学术公案确实让人有上下挂联、深文周纳的弊病。
陈寅恪“不古不今”就是在给冯友兰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提出的
考证与释读陈寅恪的“不古不今”的一个关键,是要找出与这一语词出现的时间,以及这一时间前此陈的学术研究领域。1934年陈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写的审查报告提出了自己治学的“不古不今”的说法。而此前,陈的学术注意力从蒙古史、元史、敦煌学、年历学稍稍向魏晋转移;而这些学问所涵指的,不可能用“不古不今”加以概括。那么,陈寅恪的“不古不今”究竟指代的是什么,这就需要从陈的学术背景来分析。陈寅恪从德国柏林到清华学校国学院任教,他所学的主要是当时西方(主要是欧洲)汉学界正在崛起的古代东方学,陈的域外古文字、古语言、蒙古史、元朝史、敦煌学等就是“古代东方学”所涵指的内容;从陈初到清华大学为学生所开设的课程也可以看出,他也是将自己在德国所学专业的运用,而他发表在《学衡》、《国学论丛》、《史语所集刊》等刊物上的论文,也可以很清晰地表明陈寅恪是在古代东方学领域在开展自己的学术工作。由此,我可以判断陈寅恪的“不古不今”,决不是所谓的“中古”或“魏晋隋唐”,更不是所谓的“晚清民国初期的经今古文之争的一段恩怨与学术公案”
陈寅恪手迹公开展览
晚清经学所贯彻的今古文之争,确实对中国、学术、思想、教育等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进入民国后,经学的影响了就很弱了。钱玄同、顾颉刚、胡适等人所掀起的“古史辨”运动,实际上将经学的地位彻底颠覆了。后来的尊孔读经,已经是经学的余脉了。而经学最后退入国故学、诸子学,就不复以正统与主流自居了。钱穆《师友杂忆》中所涉及到的1930年代经学,只是一种不真确的记忆,不能引为根据。
史学家钱穆著作涉笔晚清民初经学的今古文派别之争
在释读陈寅恪的经典学术时,不能想当然,不能预设结论,更不能以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位研究辛亥史的知名学者,将自己的学术视野下移到晚近学术史,自然在“大而化之”问题上有会心,但在实证上就往往走向偏门。解释陈寅恪的“不古不今”时师心自用,殊为可叹。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不古不今,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相关文章:
2.米颠拜石
3.王羲之临池学书
8.郑板桥轶事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