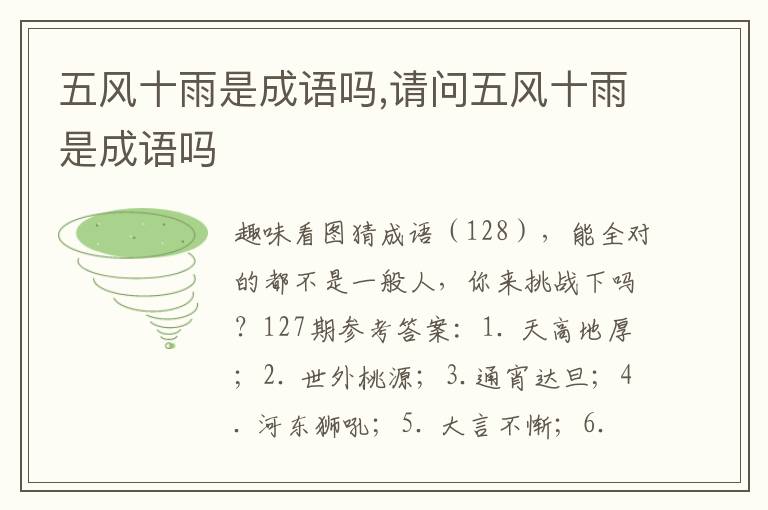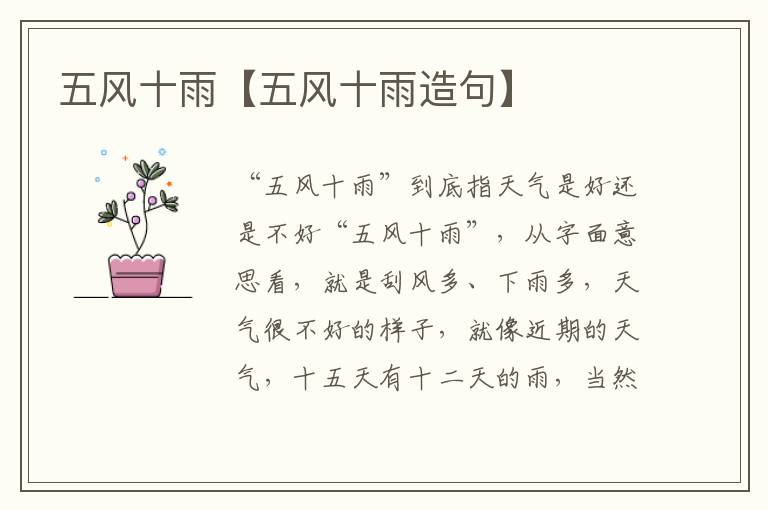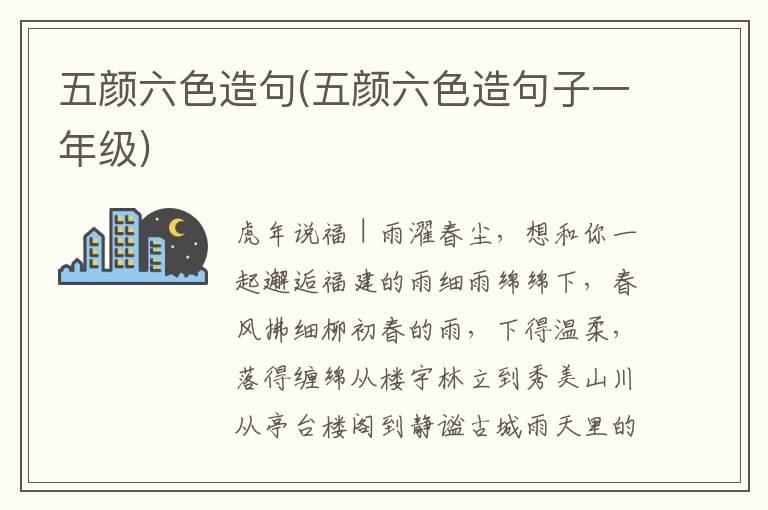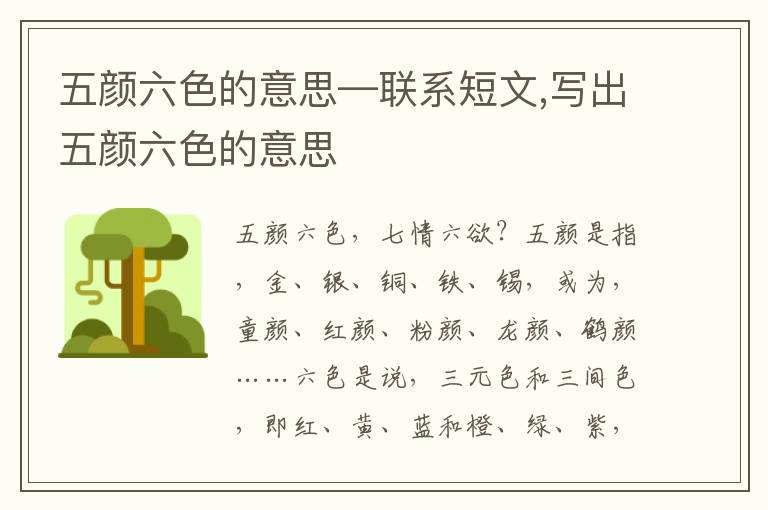“金句”里众说纷纭的张爱玲
《手绘张爱玲的一生》
作者/绘者:画眉
版本:漓江出版社
2020年8月
《张爱玲传》
作者:余斌
版本:文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
《张爱玲》刘野
今天,张爱玲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她的情感经历、日常生活、散文随笔中冒出的遐想,以及作品里被摘录的金句,这些零散的资料如同飘浮在空中的花瓣,为大众塑造出一个色彩缤纷、又空洞迷离的张爱玲。当我们一次又一次通过这种方式来举例证明张爱玲的性格时,其实却很容易陷入误区,因为,想要了解真实的张爱玲,必须回归到她的小说里,去那里找到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导语/宫子 撰文/余斌
今年是张爱玲的百年诞辰,去年年底,即有张迷以《红楼梦》中史湘云有点大舌头的发声方式,将2020年谐音写作“爱玲爱玲年”,配上张爱玲最常见的那张睥睨神情的照片,制作成海报或年历,以为纪念。可以想见,后面当还有一番热闹。
对“张爱玲热”而言,1995年或许是一个更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因她的去世,“张爱玲热”在才算浮出水面,获得正式的“命名”。其后是不断高,一浪高过一浪。倏忽之间,居然二十五年过去,张爱玲仍然可以在媒体上制造热点。
二十五年的另一个说法,是“四分之一世纪”,“世纪”似乎比具体的年头更能制造时间的流逝感。这样的时段,虽然还不足以完成文学史的淘汰,对很多作家的名声却已构成重大的考验。
1993年,我在《张爱玲传》后记中曾对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有过一番悬想:“……也许她将不仅仅属于现代文学史。遥想几十年、几百年后,她会像她欣赏的李清照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一个稳定的位置也说不定,而我们知道,那时候今天为我们熟知的许多作家肯定都将被忽略不计了。”前一条尚待时间验证,无从知晓,后一条则已见分晓:新文学作家大多已经以“文学史意义”的理由寄身现代文学史,史料价值代替了文学价值。关键是,他们不再进入当代的阅读场景,张爱玲则属于极少数仍能与当代作家争夺读者,且令后者瞠乎其后的新文学作家。尤有进者,要说仍然保持着与当代生活之间密切的对话关系,鲁迅之外,恐怕就要数张爱玲了。
说这话的意思是,有些一流的现代作家虽仍在读者的书单上,但对其作品的阅读已更多是美学意义上的,他们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标高,今日仍然可以是审美的对象,但与当代生活的指涉已相当薄弱。张爱玲不同,她固然是最杰出的新文学作家之一,以审美的标准,没几人可及,同时她的传播又远非在文学的意义上进行,她从来不是一个标榜“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却偏偏是她,以离席的方式持续地“在场”,完成对当代人生活的渗透。
她与当代生活的对话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张爱玲以她的方式参与了当代人趣味、价值的塑造,一方面是“张迷”对张爱玲添加的“人设”,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乃是某种不由分说的自我投射。
“张爱玲热”并非作家张爱玲的单一身份,她是“乱世才女”(天才作家加胡张恋中的乱世佳人),又顶着“小资教母”那“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光环。就早已溢出文学的“张爱玲热”而言,她的作家身份甚至为后两者所掩而显得模糊不清。在此,张爱玲不可避免地被大大地“异化”了:“张爱玲热”当然是从其小说、散文的传播开始,但张爱玲传奇很快将阅读行为席卷而去——张爱玲传奇取代张爱玲小说,成为关注的中心。并不是说对张的阅读已然取消(尽管大量不读张书仅凭片言只语道听途说即自认张迷的人的确存在),而是对张作品的阅读往往一厢情愿导向了传奇,而张的传奇最终凝定为一种“出名要趁早”的世俗进取心,“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的深情和毅然决然的姿态。
于是生出了一个鸡汤化的张爱玲。杰出的思想家、作家被误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如我们在网上所见,甚至尼采也可以被鸡汤化的接受。张爱玲因其小说的雅俗共赏,似乎更容易受到鸡汤化的重塑。鸡汤化可以有各种形式,最容易按迹索踪的,乃是“经典语录”或“金句”的打造。网上的各种张氏“金句”、“语录”琳琅满目,层出不穷,甚至还有种种的分类,比如“张爱玲经典感伤语录”、“张爱玲爱情语录大全”,有个“张爱玲经典语录大全”,居然有460条之多。这里面难免鱼目混珠,张冠李戴,诸如“因为平淡,我们的爱情有时会游离原本温馨的港湾;因为好奇,我们的行程会在某个十字路口不经意地拐弯,就在你意欲转身的刹那,你会听见身后有爱情在低声地哭泣。”这样的语句,资深张迷一看便知,不可能出自张的口中笔下,和张没有一毛钱关系,也就不足为害,构成“迷惑大赏”的那些带有明显张氏印记的语录,则按照鸡汤化的原则被反复征用,“货真价实”而又似是而非。
“金句”“经典语录”的制造,关键在于语境的模糊与取消,能指在空中飘荡,所指已然不知所踪。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
比如“我爱你,关你什么事?”一句,原是小说中人的对白,出自《第一炉香》女主之口。此时的葛薇龙与乔琪乔正在逛铜锣湾,由故事开始出污泥不染的自欺到同流合污的结局,其下坠的人生已画上句号,目睹英国水兵调戏雏妓的场面,薇龙黯然认命:其实自己和一样,只不过是被逼无奈,她是心甘情愿。在此背景下,乔琪乔一时良心发现的歉然激出她的这一句,乃是认命加自怨自艾的耿耿之语(怪谁都于事无补了,怪到最后还是要怪自己挡不住诱惑),乃是“小女人”式对生命的残酷的不甘却又无奈的接受。衬着薇龙不堪的处境,此中满满的嘲弄,自不待言。然而孤立出来,掐头去尾,当作张爱玲语录,立马变成了具有“大女人”色彩的爱情观的宣示,不是对主体的肯定,而是奔赴爱情的决然姿态。
熟知茨威格的读者,会觉这句话似曾相识,因《一个陌生女的来信》中女主人公在信中以“我爱你,与你无关”来描述她的单恋。相比之下,茨威格的人物身上有更强烈的女性意识,无奈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女性角色的话语不好径直塞进他口中;脑补胡张恋,让张爱玲在其笔下人物身上附体,却仿佛天衣无缝,顺理成章。很显然,相似的表述,在张爱玲这里获得了更强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当然是更给力的爱情励志语。这原是《半生缘》里女主人公顾曼桢回首年与恋人有缘无分的叹喟,虽说这是张爱玲少有的有意按照通俗小说套路写成的小说,这里定的调子也只是不胜低回的“惘然”(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经掐头去尾的征用,即调性大变,一变而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式的执着坚定或自我感动。
即使货真价实的张爱玲语录,在“金句”中也会被赋予新意。上引最长的一段文字出自张的短文《爱》,当然是她的直承式表达,然而如果我们对张有完整的认知,便会了然语句中流露的对“相遇”低调的郑重源于苍茫荒凉的背景,而众多张迷一厢情愿拥抱的,却是“相遇”的浪漫。
张爱玲对人生对爱情固然不是没有一点肯定,但更多的是怀疑,或者说,她的肯定是自定义的,与通常的理解实为两事。所以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曾经让许多张迷有一厢情愿的期待,因为张对友人如此这般描述这部小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媒体自然对此大加渲染,结果待书出版,一读之下,大大的幻灭,——他们没看到期待“热情”,想象的“百转千回”也完全不是这样。足见大众关于张爱玲的想象与“本尊”之间的距离。
“金句”、“经典语录”有它自己的一个系统,那些从上下文中抽离出来的语句嵌入到一个新的语境中,尽管空洞、含混、抽象,可以自由填空,容纳了种种不由分说的自我投射,且总能自洽,广义上说,这个语境是存在的。这是一个鸡汤化的语境,其归旨,或则情感励志,或则自我感动。
撕标签的张爱玲才是真实的
但在“张爱玲热”中,作家张爱玲其实是一个次要的存在,一经混编,出现在“金句”、“经典语录”的语境中,那些随意堆积的句摘不经意间就有了人生感悟而非文学鉴赏的导向,最终成为通向张爱玲其人的路标。这样一个栖身于“金句”之中的张爱玲有时甚至会被戴上“时代女性”的冠冕,然而不管出于怎样的表述,在众多张迷的心目中,张爱玲的确是因应这个时代的一个“典范”,在一个务实的、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这个接纳了种种自我投射的张爱玲比其他“民国才女”更有资格接受膜拜。
没有比这更大的误会了:事实上极少有中国作家像张爱玲这样,拒绝向读者提供各种形式的心灵鸡汤。心灵鸡汤的本质是对幻象的一往情深,张爱玲所要做的恰恰相反,就是要向人们呈现种种的:男女之情的,人性的,人生的,上海的……而这个,黯淡、冷硬,甚至残酷,用她自己的句子描述,是“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自我投射的幻象,是与各种刻板印象,各种标签叠加在一起的,张爱玲则是一个近乎执拗地不断撕下标签的人。
读各种励志故事长大的人,读她的处女作《第一炉香》即有“霎时间天昏地又暗”的跌落感,因葛薇龙的堕落故事简直像是在给“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悲伤”这句话加注。关键是张爱玲认定,不存在罪恶社会与善良无辜的个人的二分法,薇龙的悲剧蕴含于她自身,现实就是肮脏不可理喻的,而人就是这现实的一部分,从而基本上让我们杜绝了自怜的可能。
《倾城之恋》因其大团圆的结局为人乐道,似乎大可成为一则“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佳话,张爱玲掰开揉碎了给你看,其中有多少精细的算计,多少悲伤的无奈,灾难降临促使男女主人公抱团取暖的阴差阳错,反令表面的喜剧结局露出人生更大的不圆满。女主人公在理当满心欢喜的当儿生出莫名的惆怅,疑惑世上“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这才是张爱玲要揭示的男女情感的,“倾城之恋”的命名亦因此充满反讽的意味。
很多年以后发表的《色,戒》,张爱玲把一出理当高潮迭起的谍战美人计还原为世间普通男女的感情戏。王佳芝的捉放曹,在她不啻殉情之举,张爱玲却意在点破,她以为对方爱着她,不过是入戏太深的一厢情愿,自怜自恋而生的幻觉,她的亦因此变得毫无意义。此中凛冽的审视不但一般读者难以面对,大导演李安也不能接受,以至电影《色戒》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以承认易先生的友情为前提,赋予了这残酷故事些许的暖色调。
相对于小说中泠然的悲剧意识,张爱玲在散文中的姿态要柔和一些,显得更入世近俗,但是她对的执着同样贯穿其中。世人眼中的上海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她眼中的上海却有异样的荒凉感:
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偌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一长排窗户,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帘子,像文艺滥调里的“沉沉夜幕”。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锐叫,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哗!哗!”渐渐远了。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
用“张看”观察到的
不妨说,张爱玲的作品,从早期到晚年,有一个执拗的声音始终相伴随: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这个声音曾以很直白的方式出现在《第二炉香》中。事实上,她在香港时的速写已然微露此意,有一系列男男女女的漫画,她给一一配上文字,“他也会”“她也会”,如何如何。足见道出她对的发现是她的一大兴奋点。早年的作品中,我们能感觉到某种按捺不住的表而出之的急切冲动,证据是《传奇》中不时出现的议论,有时是借人物之口,有时干脆直接登场。她发现的令人悲哀,发现(用她的术语叫“张看”)本身却让她兴奋不已。
到晚年,这份急切与兴奋消失了(正像“出名要趁早”的欣喜消失了),对的执着却一仍其旧。某种意义上说,她最后一部小说《小团圆》是对胡张恋的还原,对母女关系的还原,对自我的还原,从普泛到具体,都是勘破的努力。
逼问在张爱玲已成至高原则,为了逼近,她甚至不惜连自己也搭进去。在这一点上,张不能说是与生俱来,却是早已如此,于老为烈。她在《私语》记录上中学时母亲与她告别一幕时即有对一己情感的怀疑:“……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假如这里的以今视昨因调侃的语气显得轻松,那《烬余录》对她港战中当看护时扮演角色的描述就显得耿耿于怀了。她写到了对一个伤口溃烂的病人的厌弃与逃避:“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忏悔的张爱玲,轻易地忏悔往往以自我感动而告终,对她而言,重要的不是道德审判,而在于,人性的必须直面,每个人都是人性的证明。在《小团圆》中,她的自我审视达到极致,让人震惊于她对自我的揭示,只能说,她的心狠手辣少有人及:她对自己真下得了手。
挑剔、审视的目光构成了张爱玲洞察力的标志(后面当然是她的怀疑主义),在她那里,审视最终发展成逼视,在世人因现实的肮脏、不可理喻而收回目光,回到有意无意的自欺的地方,她目不错珠地盯着看。这样的张爱玲事实上是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必须将张爱玲纳入想象的舒适区,放大她与舒适区能够重合的部分,以入世近俗的张爱玲遮蔽那个毫不留情逼视人性的张爱玲,她才有机会扮演人生导师,甚或“时代女性典范”这样的角色。金句里的张爱玲,不妨看作一个缩影。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张是个不惮于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的人,孰料大众又将这面纱捡起,罩在了她身上。
“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要算张爱玲词典中最容易被人提及的术语之一。这个很张爱玲的表达在《金锁记》中出现了两次,都和长安的心理活动有关,一次是她选择休学,一次是她放弃与童世舫的婚姻可能之后。上学、恋爱是她出现人生转机仅有的两次可能,皆因七巧的破坏弄得乌七八糟,两次退缩,主动选择放弃,都是幻想能在同学、恋人心目中留下一个凄美的形象。张爱玲于此两次调用“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其于长安自我感动的反讽,至为明显。她固然同情长安的命运,但对其虚幻的自怜自恋,决不心慈手软,放弃讽刺。可惜她无情的反讽常被放过,而“手势”却是耽溺性的。
当然,你如果硬要说,在终极的意义上,张爱玲的人生,甚至她的写作,也不过是一个这样的手势,我们倒也无话可说。
初心|郭启宏:给再多钱也不写乌七八糟的东西,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就值了
前不久上演的北京人艺年度大戏《杜甫》,因为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杜甫而引发。对该剧编剧郭启宏而言,这也是他创作生涯中重要的一环,从《》到《杜甫》,从“诗仙”到“诗圣”,他的诗之江湖完成了最重要的描摹。翻阅几十年来的《北京》,我们曾用一篇篇新闻报道和评论,记录着这位潮州籍北京编剧的成长之路,从京剧《司马迁》到评剧《成兆才》、昆曲《南唐遗事》,再到话剧《》《知己》《杜甫》,没有一部作品不曾受到。
01 当初做编剧是“赶鸭子上架”
1940年,郭启宏生于广东饶平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在家中接受古典文学熏陶的他,1957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彭真感觉北京市文艺团体创作者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因此决定从全国重点大学中招收优秀的毕业生充实各个院团的创作力量。工作人员先到北大、复旦、南开、中山、武大等高校摸底,了解哪些毕业生比较优秀,结果中山大学老师就推荐了郭启宏。
来到北京后,从没有看过一场评剧的郭启宏,被分配到了中国评剧院。对戏曲几乎没有什么认识的他,就被这么“赶鸭子上架”,服从分配当了戏曲编剧。郭启宏做学问比较老实,不会写戏那就多看。
郭启宏
剧院给了他一张月票,每天去中国评剧院管理的大众剧院看戏,剧院下场门有个放器材的小房间,就成了他的专属座位。“我心里想着党分配我干什么,我就要把它干好,一定要做一个好编剧,所以几乎每天都去看,同时还要看大量的书。”对郭启宏而言,戏剧的结构比较难,至于大家都很怵头的唱词,古典文学功底扎实的他倒并不担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郭启宏的父亲和哥哥双双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年仅48岁的哥哥戴着“右派”的帽子去世了,去世后几个月才被“拨乱反正”。哥哥的离去让郭启宏十分悲痛,父亲和哥哥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也让他联想到了中国上的众多知识分子,即使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仍然忍辱发愤,为中华文化留下灿烂的遗产,比如遭受宫刑而不改其志坚持完成《史记》的司马迁。
心有所动就奋笔疾书,郭启宏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就这样开始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写出了京剧《司马迁》,因此有了“快手郭”的名号。身在评剧院,第一个原创作品选择京剧,是因为他觉得京剧的艺术形式更完整,演员选择余地也更大。作品通过之后,在只有9平方米的家里,郭启宏彻夜未眠,和妻子抱头痛哭,“那感觉就像是终于重见天日了。”
1980年,《北京》报道《司马迁》的评论文章
几经波折,这部作品被搬上舞台,一炮而红,获得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二等奖。《北京》1980年1月6日刊登的评论文章称这部作品“着力塑造了一个见识卓绝、善恶分明、刚直不阿、坚韧不拔的史学家的光辉形象。这是剧创作中的一个新收获”。正是从这部作品开始,自发创作成为郭启宏的创作常态,他借抒发个人胸臆,成兆才、白玉霜、王安石、李煜等一个个人物在他笔下“复活”。
02 创作《》融入自身境遇
年,郭启宏调入北京人艺。一个戏曲编剧被调入话剧院团,可以想象当时北京人艺对人才的选拔不拘一格,而郭启宏也如鱼得水。对他而言,光写戏曲很难得到满足,“戏曲在反映生活的现实深度方面,不够丰富也不够尖锐,不能触及到本质的东西。”但戏曲程式化的表现形式也自有它的美,他希望在自己的创作中,“既能保持话剧的深刻性,也能有戏曲的自由。”
《》剧照。李春光 摄
在北京人艺,郭启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院长于是之总是问他想写什么,大家可以出点主意。但习惯于自己创作的郭启宏不太习惯这种创作方式,只是摇头说还没有。其实,当时他正因为个人的境遇而决定写话剧《》。
被称为“诗仙”,留给人们的形象就是飘逸洒脱。郭启宏认为那是因为人们并不真正理解,“其实他没有那么洒脱,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在那样的社会里,有底线的人肯定就无法洒脱。”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话剧作品。
《北京》对话剧《》的首演报道
当他写完整个剧本后,交到了剧院。谁知道,于是之拿到剧本后,有半个月没有找他谈。毕竟是自己在北京人艺的第一个剧本,郭启宏心里非常忐忑。过后,他才知道那段时间,于是之无论去哪儿,随身都会带着的资料翻看。
有一天早晨,家人已经去上班了,郭启宏还没起床,就听到有人敲门。一开门,刚刚晨练结束的导演苏民,一身短打站在门外。进了屋后,苏民就兴奋地说:“我看到了一个好剧本!”“谁的?”郭启宏问得有些心不在焉。“你的!”原来前一天晚上,苏民刚看完《》的剧本,就兴奋的不得了。对郭启宏而言,国学功底深厚的苏民,的确是导演《》的不二人选,已经退休的苏民也因为这个戏而重新燃起创作热情。开始排练前,他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起沿着长江,重走当年走过的路,那段时间他们的话题只有。
今天再提起当年和苏民的合作,郭启宏坚持认为,“《》的生命力如此长久,有剧本的基础,也有导演的发挥,如果不是苏民执导,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和效果。”
《北京》对话剧《》获得文华奖的报道
转战话剧领域的郭启宏,第一部话剧作品又是一炮而红。话剧《》1991年年底公演,1993年即获得五项文华奖,包括剧目、编剧、导演、舞美、表演奖项,1993年11月27日的《北京》头版记录了这一重要时刻。纷至沓来的荣誉,不仅让郭启宏对自己有信心了,也意识到“北京人艺这个剧院能够实现我的追求,让我能创作出真正的杰作”。正因此,郭启宏不愿意由人艺之外的剧院来演他的话剧作品。他迄今为止创作了九十部作品,其中只有七部话剧作品,都是给人艺写的。
03 写剧观照当代人的心灵
1995年2月17日,《北京》发表的一篇人物文章中用一句话肯定了他的创作:在剧领域有“小郭”之称,“”指郭沫若,“小郭”就是郭启宏。
“写什么东西必须把自己摆进去,不把自己摆进去就没有真情实感,就没有创造性,没有反思……”总结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经验时,郭启宏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虽然他的作品中题材居多,但他认为,“不过是一个挡箭牌,题材也可以更曲折幽深地表达作者的个人愿望,艺术作品要是不能表达个人愿望为什么要去写?”正如他因为哥哥的遭遇写了京剧《司马迁》,因为个人境遇写了话剧《》,在他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投射着自己的影子。
话剧《天之骄子》首演后,郭启宏发表于北京的创作刍言
书生气十足的他,常常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时,他写了昆曲《南唐遗事》。在他看来,李煜这样的人是当不了皇帝的,其悲剧在于错位的人生。后来他的话剧《天之骄子》中对曹植的勾勒,也是因为当过院长、下过乡的他,发现自己不是当的材料后,内心自觉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1995年1月28日,郭启宏在《北京》发表的《〈天之骄子〉创作刍言》中提到:“曹氏兄弟已经过去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他们的人生历程却被后世人无数次地重复着。我想起北宋清满禅师的一句禅语:‘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其实梁与柱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正是通过话剧《天之骄子》,郭启宏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可以做梁的做梁,可以做柱的做柱,不能做梁做柱的还能当柴烧”,他的心里也就轻松了许多。
大家都说郭启宏擅写剧,可他却觉得剧、现代剧这种只是着眼于题材的分法并不科学,“所谓的剧、现代剧,其实只是运用的材料不同,对编剧来说,创作方法、思维方式是不分和现代的。剧写的其实也是当代的事情,只不过是原材料来自于,其实抒发的是当代人的胸怀,编剧是当代人,观众也是当代人,不观照现实的不能给人的心灵任何影响,那就是失败的。”他将自己创作的剧称为“传神史剧”,重点在神而不是形,“我觉得只是剧的躯壳,灵魂还是剧作者要表达的对当代的思考。”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己也是知识分子,郭启宏的笔下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尤其多,他坦承,“写下里巴人不如写阳春白雪来劲”。他也以冷静的笔触剖析这个群体,“我爱知识分子,也知道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问题。”
《知己》首演后,郭启宏在《北京》谈创作的报道
2016年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国际戏剧节从北京人艺提供的众多经典剧目中,邀请了《知己》去圣彼得堡演出。在他们看来,这部作品写出了跨越国籍的人性,是俄罗斯观众也能真正看懂的戏。这部充满文人意趣和思想光芒的作品,正是郭启宏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一次深入思考。
回首几十年的创作道路,经历了那么多的起起伏伏,年近八旬的郭启宏慨叹,创作这条道路并不好走,“但我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写,哪怕给很多钱。”眼下,他手里还有一部戏在写,“写戏是我生命所必需的,从其中获得快乐,体现人生价值。我一辈子把这一件事干好了,就值了!现在看还行,我没有辜负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END-
本期作者:牛春梅
本期编辑:王广燕
本期监制:周南焱
【乌七八糟-乌七八糟什么意思】相关文章:
2.米颠拜石
3.王羲之临池学书
8.郑板桥轶事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