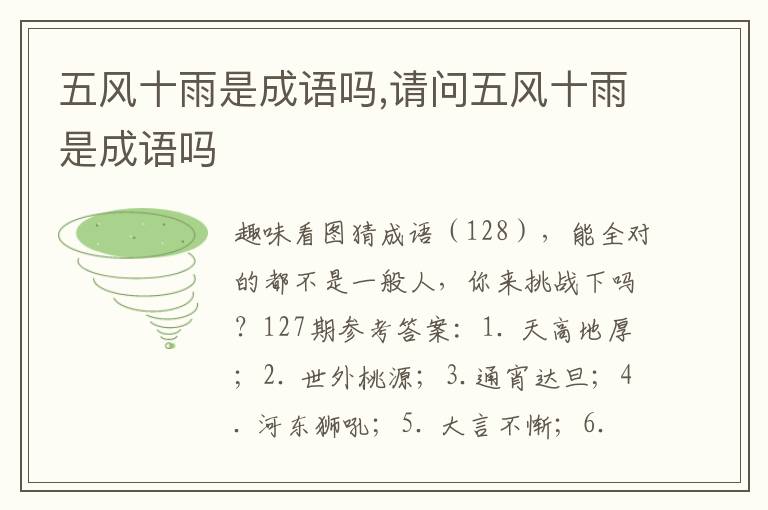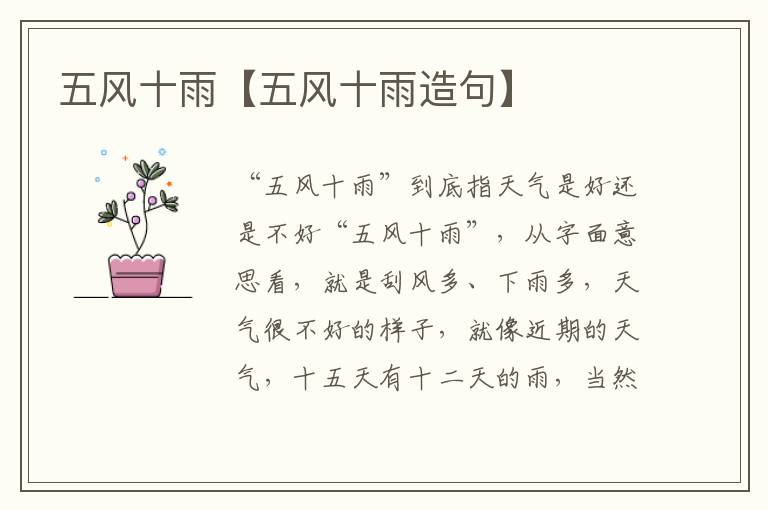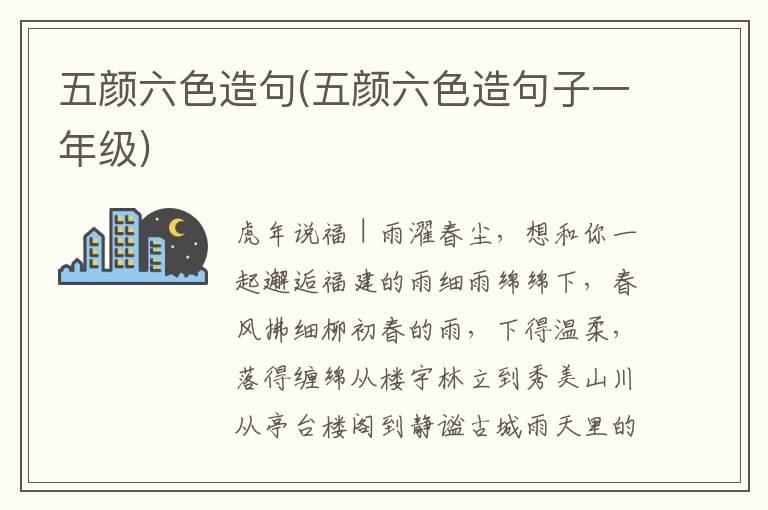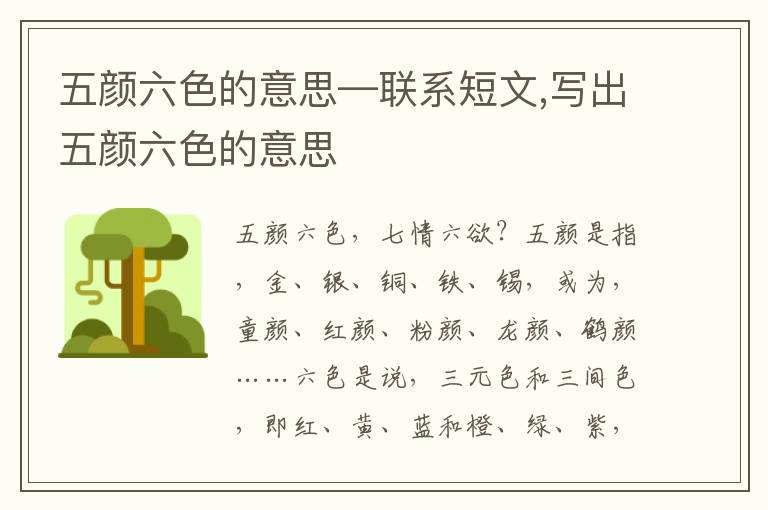上初中时,语文老师给我们讲,“家”字为什么是宝盖头底下一个“豕”。因为在远古时期,猪是跟人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屋里没有猪,就不能称其为家了。
睁着眼说瞎话嘛,还远古时期,其实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我的家乡,猪仍是跟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起码我家是这样,邻居家也是。
我跟奶奶睡西房,猪睡东房北半间,南半间是锅灶,当中只以半段矮墙接半道木栅栏隔开。不光住同一座房子,猪也跟我们用同一口锅吃饭,当然,吃的是不同的东西,而且它们每天比我们少吃一顿。虽说是同吃同睡的伙伴,到了年底,照例是要把它们杀了吃肉的。对此我们毫无怜悯或愧疚之意,自然规律嘛,习惯就好。我家一年只养一到两头猪,一律是约克夏大白猪。麦收时节抱崽,养上大半年,正好宰了过春节。
我家曾养的猪留给我的最鲜明的集体印象是:一到青春期就被强行戴上一枚亮闪闪的钢丝鼻环,加上它们饿了就扯开嗓子嚎,十足的朋克范儿。王小波写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读到那篇文章时,我立刻就想起来,我家也有过一只拥有闪耀时刻的猪。当然了,它的觉悟和壮举还达不到小波老师笔下那位“猪兄”的水准。它并非有意识地尝试突破人类对其生命的设置,只是受不了我的凌虐而做出了本能的反抗。换句话说,它算不得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仅仅是一只被逼上梁山的猪。
每个男孩大概都做过策马奔驰的梦,我也不例外。我的心里住着一匹骏马,可惜我的家里没有草原和马厩,我们村里、乡里乃至县里也没有。我只见过马戏团那种脏兮兮、蔫耷耷的马。别说不是我的,就算他们主动牵给我,我也不敢骑。事实上,我连队上的水牛都不敢靠近。我寻思着,相比于山丘一样的牛和马,我的身材还是跟家里那头猪比较般配,于是便打起了它的主意。
一个初冬的下午,奶奶下地干活去了,爷爷钓鱼或者搓麻将去了。我意识到机会来了,就立即关上屋门,走向猪圈,打开木栅栏,准备进去骑那仅有的一头猪。可猪圈里积着许多猪粪。我却步了,抄起一根竹竿往猪背上招呼,想把它赶出来。它抗拒了老半天,终于扭扭捏捏地出來了,停在我面前,仰起脖子,用哀怨的眼神瞟我。它的背脊上粘着一些粪便,我不敢直接骑上去,只好去房间抱了一床被子过来,披在它身上做“猪鞍”。
到此时为止,它都非常温顺,几乎一动不动,任凭我发落。然而,就在我骑到它背上的那一瞬,它发飙了,一下子将我掀翻在地,接着撞倒一把椅子,拱开大门,冲了出去。完了,要闯祸了。我连忙爬起来追出去。它径直奔向晒场尽头,穿过东西大路,钻进了河岸的灌木丛。见我追了上来,它索性横下一条心,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麻利地朝河心游去,然后就在河心来回巡游,歪着脑袋观察我的动向。我顿时傻眼了。我学了那么多次都没学会游泳,它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但我没工夫自卑,我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一头猪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如果它淹死了,我可怎么向奶奶交代呀?于是我认了,讨好地向它招手,请求它上来,保证不再骑它。但它已经不信任我了,固执地在河心逡巡。我顾不得要挨骂,决定去找人帮忙,但在找人之前,我先匆匆溜回家,将猪圈的木栅栏关好,为撒谎埋好伏笔。其实用不着我去叫人,在河边洗衣、洗菜、洗粪勺的邻居们,早就发现了这头会游泳的猪。
消息迅速扩散,不久,河边就三三两两站了许多人,都在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一会儿奶奶也来了,笑呵呵地问这是谁家的猪。我告诉她是我们家的。她愣了一下,赶紧叫了几个小伙子帮忙把它弄上来。一道冲它喊,不管用;用长竹竿拍水,不管用;向它扔泥块瓦片,还是不管用。这条河里又没船,怎么办呢?大冬天的,总不能让人下水去抱猪吧?最后,一位大哥想出了个好主意:搬来两只洗澡用的椭圆形木桶,并排摆好,将一根竹扁担居中横在桶口,用粗麻绳固定,这样就有了一条左右对称的“双舱船”,勉强可以载起一个成年人。那位大哥亲自坐上这条“船”,小心翼翼地用手拨水,慢慢向河心的猪划去。我们在河岸上注视着,都替他捏着一把汗,生怕那条“船”重心不稳翻掉,或者被猪拱翻。幸而这两种担忧都没有发生,猪也被他成功撵上了岸。它哆嗦着一身肥膘,乖乖地踱回了熟悉的猪圈。我和奶奶都松了一口气。它大概也松了一口气。
后来我有没有受罚,我完全记不得了。我一定谎称是猪自己跃出猪圈的。而那条粘了猪粪的被子则无声地揭穿了我的谎言。但这又怎么样呢?顶多挨一顿骂而已。我只是干了一件蠢事,奶奶不可能杀了我,我毕竟是人,而且是她的孙子。而那头猪呢,尽管拥有了一个辉煌的下午,展现出了一个游泳健将的天赋,可谁会珍视它这多余的天赋呢?它只是一头猪啊,专心长肉就可以了。作为一头生活在猪圈里的猪,它是注定要重复前辈们的命运的。没错,它没有活过那个辉煌的冬天。
【一只被逼上梁山的猪】相关文章:
2.米颠拜石
3.王羲之临池学书
8.郑板桥轶事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