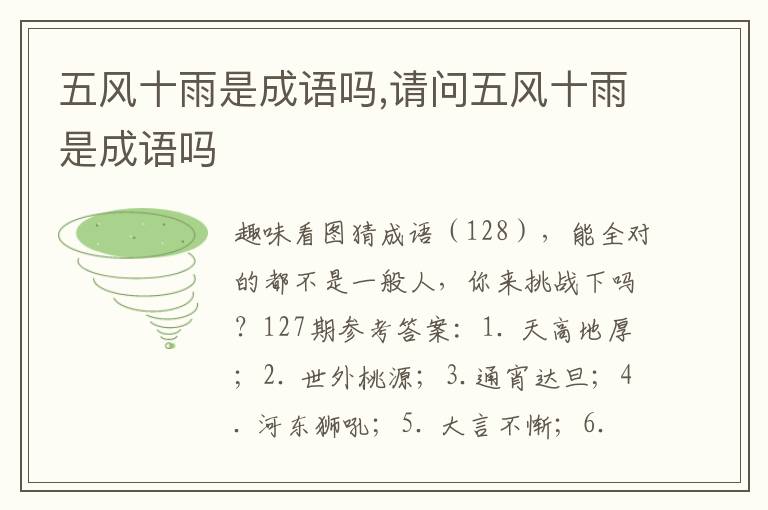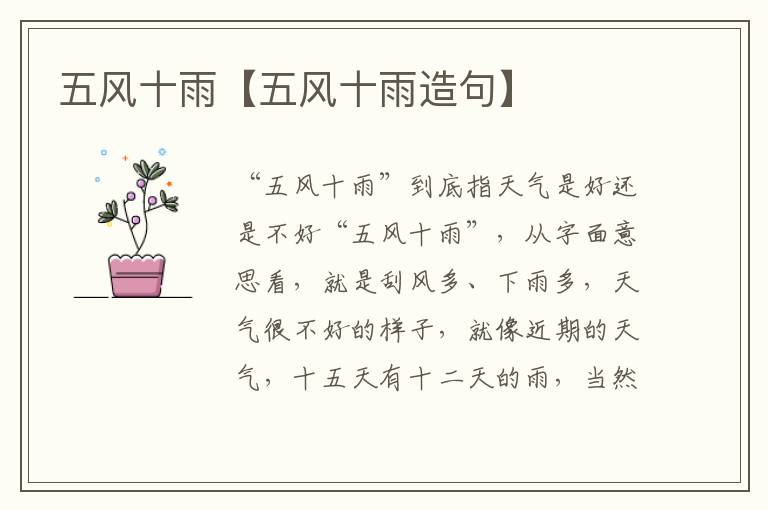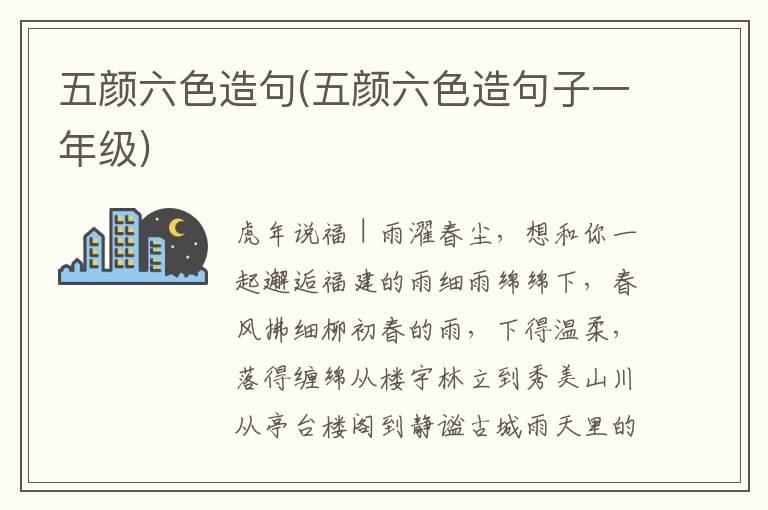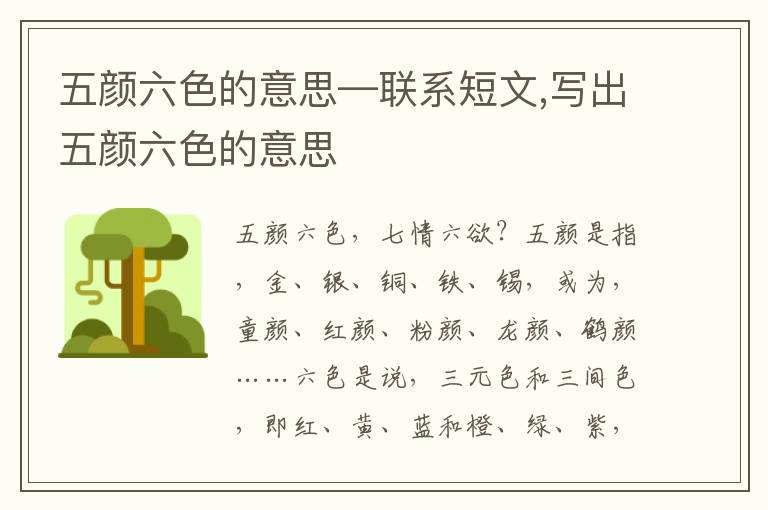当小孩的时候,我愿意做一朵很小很小的野花骨朵,躲在路基旁、山坳里、慢坡下的随便什么地方,一下子开出一朵很美很美的小花来。用不着谁看见,也用不着谁欣赏,自然会美呀美呀的,翘着小手指,咧着嘴角,学戏里的莺莺小姐般的扭腰扭胯地走路,憋假嗓子说话,支使人儿。象一朵长在细嫩竿子上,被风抚养得再舒服不过的小粉花,对着太阳摇啊摆啊的,又自然,又快乐。
大一点了,作个少年人,我希望做一条鱼,整日里欢蹦乱跳,强健有力,出溜稀滑,满世界撒野,疯,什么正经事也不干,谁也抓不住。一天到晚闪闪烁烁瞪着大眼四处打探,哪有大海,大海有多大,大海有没有边,怎么才能掉海里,掉海里可就自由了,想管的人这辈子是管不着了。但绝对不懂这样焦渴的向往,可以被称着理想,也可以被唤着幸福。这个年龄幸福最多,可惜不认识。再说,整日里忙着玩完一个再抓一个地玩,根本顾不上幸福不幸福。
青年人了,我想做一棵树,做一棵高大、挺拔、傲岸而又正直的大树。集千种优点于一身,汇万般理想于胸怀,没有一个瑕疵一根多余的枝杈。铮铮硬骨是正气凛然的化身,也是高高在上谁也瞧不起的资本。一头浓密旺盛的绿叶,更是骄傲的宣言,胆敢接下满世界的阳光,满世界地呼风唤雨,以此作为对太阳的回报。总之,勇敢而又傻气,冒失但很可爱。当然,我还经常渴望能做一棵咔吧作响,正在倒下去的大绿树。很壮烈,很英雄,很无畏,很理想,大滴的树浆浓于血,死得时候没有眼泪只有国际歌。也常常很脆,很有限,很能瞎操心,死的很稀里糊涂。
老一点了,我愿意做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尽管我非常清楚我做不了白胡子老头,要做也只能做个白头发的姥姥奶奶。我做不了白胡子老头还因为,我非常地喜欢做女人。虽然吃够了做女人该吃的一切苦,苦苦地逃不出做女人的樊笼,想到来生来世如能再投胎,还是觉得做女人才会比较喜欢自己,与我的风格也比较合适。但是,做白胡子老头是幼年的理想。感谢上帝,还有那个幼年的印记能守侯到现在,算得上是个好造化。我希望老的时候,极其聪明,智慧而又博大,满腹经纶,深谙世事。面有狡猾之光,嘴挂斜斜微笑。人生对他很难再有欺骗,因为上当已不大容易。他终于有了一副旁观者从容自得的尊容,和一把经过岁月梳理的白胡子。就为这样的睿智,我不愿意放弃做白胡子老头的愿望。快死的时候,我愿意做一个生在缓慢向阳坡上不甚光滑、不甚规整的大石头,而且是褐皮的。太阳一出来,周身太暖。太阳要落没落,它先已冰凉,浑然沉默着木然无知了。如果有个什么人,具体的什么人倒无所谓,极其偶然地来这样的石头上一坐,歇一歇人生的疲乏,大石头会无动于衷,任人来去自由。碾得太厉害了,也还可能懒懒地翻动半只眼皮,乜斜上一眼,终于无话,就又似睡非睡而去,像是个真正不拿人间事当事的神仙。
死了以后,最好的愿意是当一粒干净的土,学名叫团粒结构。但条件是要绝对的干净,不遭人践踏,不被人污浊,还要绝对地不被搅扰。这样的土,想来想去,必须是在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想来想去,凡是人到不了的地方,竟都有些不受污染清净单纯的好处。所以我想做一粒和黄山大兴安岭的土挤在一起的土,暖暖的,沉沉的,非常安全,听得见水欢鸟叫,闻得见松油芳馨,由此,闭上眼也笑的舒心,满当当堆他一脸惬意。我当然知道,这个愿意寸步没有逃脱风水先生的掌心,也有点不求上进颓唐的堕落。人生很累,所以我仍然喜欢有个死后贪图享乐的愿意。
说来说去,唯独现在愿意什么没有说到,也唯独现在我没有愿意。这个年龄,究竟愿意点什么好呢?
愿意是一朵小花行吗?不行,因为我已经老皮皱脸地成了一棵歪脖子树。继续愿意做一棵大树?也不行,骄傲没有了大树也就倒了。连鱼都做不成,鳍都断了,被绑在固定的位置,只能上下左右可怜兮兮地翻白眼,哪还敢想那个动人魂魄的游?也许现在,我只能做一块胶皮糖。给谁踩一下踹一脚都没感觉,谁来挖一把拉扯一下也无所谓。两头一抻,待死不拉活地滴溜当啷,眼瞅就没气了,一松手,秃噜又缩回去,一点不耽误好死不如赖活。不会哭也不会笑了,紫皮厚脸的,只会木着。还会趁人不备,忽地偷偷摸摸粘上去,碍你一家伙,给你来点小不舒服,出口闷气。还会干什么呢?
我是真不愿意做胶皮糖。可我得实事求是,不愿意难道我就不是吗?所以,论及现在,我也只好说,我愿意是一块胶皮糖。
【我愿意……】相关文章:
2.米颠拜石
3.王羲之临池学书
8.郑板桥轶事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