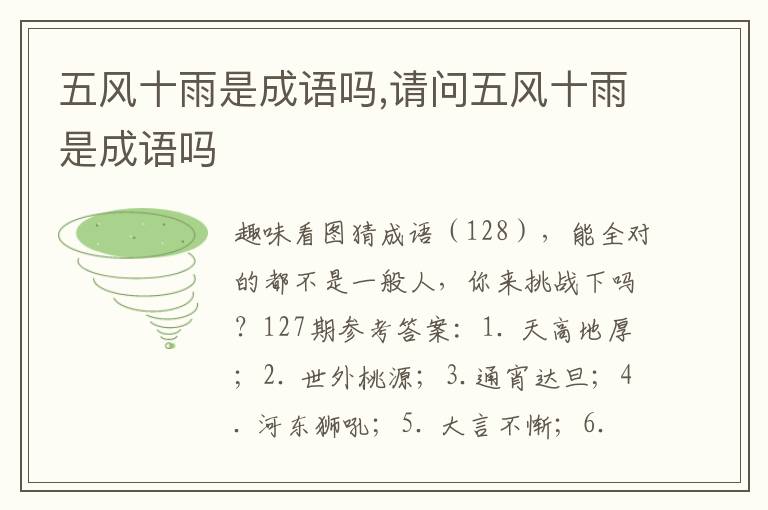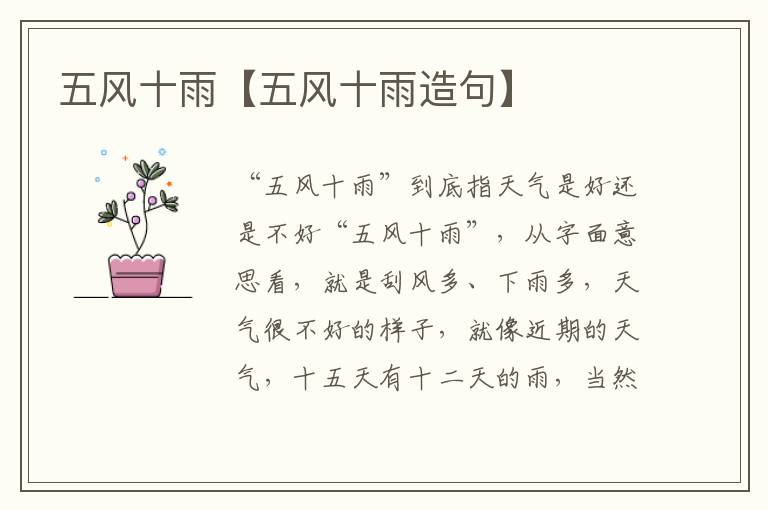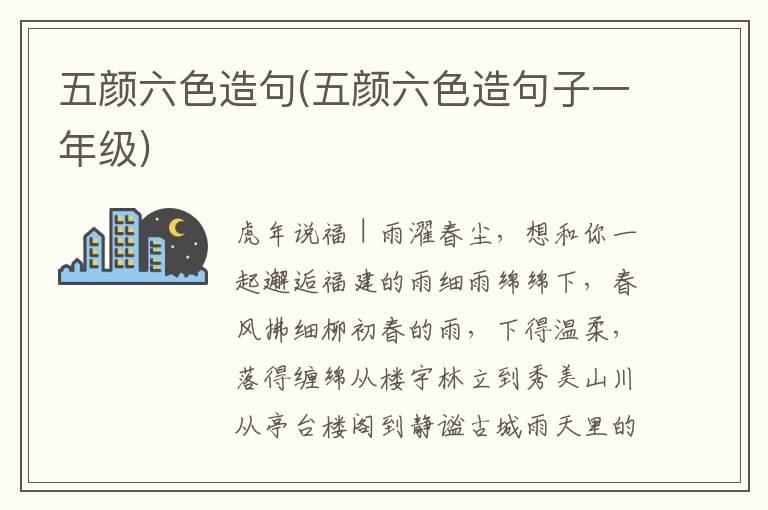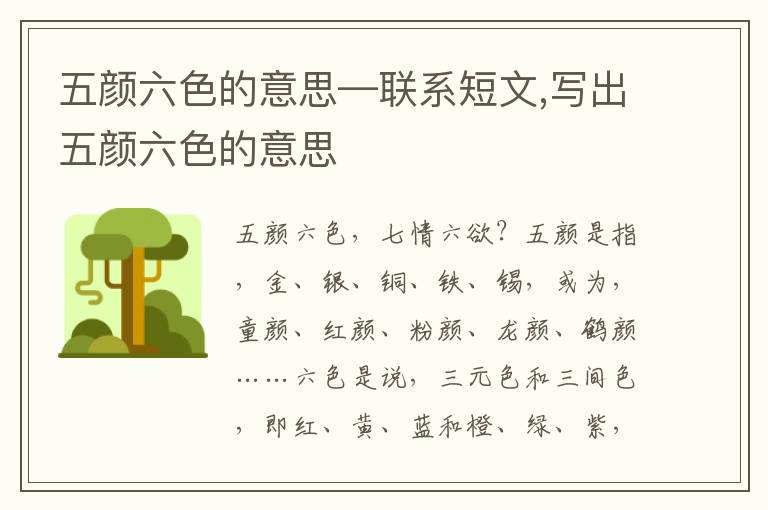把这件事叙述出来的想法,已经折磨了我两年时间,由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开头,只能在心里一次次萌生,又一次次夭折。一直以来,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实际远非如此,讲述它需要勇气和时机。
那天凌晨,我再度失眠。我明白那些基本的事实根本无法回避,否则这个故事会显得奇怪而突兀。只叙述事实,这就是最恰当的开始。这是一件小事,在别人眼里或许不值一提,对我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零零三年五月,我生命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在患病和手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弃世而去。他的死,扯断了我与老家联系的那根温热带血的脐带,从情感上切断了我回家的道路。当然,那些道路依然存在,只是我丧失了回去的理由和冲动。勿庸置疑,我与老家血肉及精神上的联系,完全因为父亲的存在。他身后留下一个完整的农家小院,如今变得空阔寂寥。那些树木花草,包括他亲手种下的山楂树,全都憋足了劲疯长,然而,再也得不到他的呵护和垂怜。
他身后还留下另一个女人,他的续弦。他与她一起生活了十二年。当我回想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时,印象如此遥远、苍白。她没有给我留下哪怕一点让我觉得亲切和温暖的感受。当然,我没有理由苛求什么,现在更不想。他们在一起生活过,这就够了。我与她之间原本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我的生母先我父亲而去。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相聚间隔了二十三年。现在,父母的团聚表现在一个传统的缅怀和纪念方式里:他们的遗像被我安置在上房正中的方桌上,他们紧挨在一起。我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回到城市我的家。
让我没有想到和无法理解的是,一天深夜,那个女人突然从床上坐起,歇斯底里破口大骂起来。这是在安葬父亲不过十天的日子里。她住在东耳房南头,我妹夫为了跟她做伴,也为了家里的安全起见,临时睡在北头的一张床上。他听到了她毫无道理地对我远逝的母亲的辱骂。父母在一起的遗照让她恼怒不已。她咒骂我母亲凭什么在这个家里占有一席之地。她使用了乡村最难听的话,一直骂了一个多小时,至到觉得解气,觉得累了才罢休。她在我母亲去世十年后,才来到这个家里,而我早已娶妻生子。母亲养育了我,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多年后,不明不白地遭受诅骂,让我难以接受。为此,我从市里赶到北李庄,一个离我老家十三里的村庄,找到那个女人惟一来往的兄弟,提出我的愤怒和抗议。他答应过问此事。他随后赶过去问询,但她矢口否认。
他向我通报了这个意料中的结果。
为了避免伤害我感情的事件再次出现,我采取了避让态度。我与妻子商议将父母遗像挪至我们结婚的西耳房。我的想法受到村邻的揶揄和否定。他们肯定上房的位置是仙逝的父母应该享有的,放在西耳房根本说不过去。我不再犹豫。那女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她在河边洗衣时还不甘心地声称,要将我母亲的遗像扔进河里冲走,但始终没敢实施。
父亲身后的储蓄代办站已不可能在家里存在下去,我让妹妹从她婆家搬过来,另租了一处房子,接手父亲的事业。父亲生前一再叮嘱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那份工作,当然妹妹完全有理由占用父亲留下的房子,那个独立的院落,至少有十四间房屋,法律也赋予了她这个权力。然而,鉴于父亲患病期间,女人对我妹妹的挑剔、排斥以及毫不掩饰的刁难和欺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决定放弃。
事隔半年,一切仿佛风平浪静。我的散文集《在沉默中守望》出版。市电视台“点击生活”栏目组拟拍摄一集专题,编辑小吕和摄像小徐一同到我老家取镜头。
我熟悉的、本该自由进出的大门紧锁,将我挡在门外。我没有进家的钥匙。大门钥匙,我房间的钥匙,全都寄放在女人那里,她到她闺女家去了。我并未觉得意外,顺当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好在后来我还是走进了那座熟悉的小院,这是因为同村的医生于涛,他租住了三间南屋,面朝大街开门,东山墙一扇窄门与院落相通。有人帮我找到了出诊的他,结束了我在门外的尴尬。
一切是那样熟悉和亲切。只是见不到父亲的身影,听不到他关切的问候,也感受不到他的气息。我开不了房门,进不到屋内,进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只能隔着门窗玻璃向里面张望。蒙尘的玻璃模糊了我的视线,屋里的摆设变得陌生,我心里泛起难言的滋味。
我们坐在院子里,于涛端来了热水。邻居们知道我回来了,都过来看望。大家坐在父亲手植的山楂树下说话。
那年的山楂特别多,特别好,跟头年正好相反。父亲病着的时候,连树也没有生机,枝叶干涩,果实小而瘪,像遭了大火。事后我才意识到,它们可能透露了父亲即将患病的信号,可惜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小院景致吸引了两位生活在城市的编辑和摄像,他们站在山楂树下,为一树小灯笼激动不已,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我从邻居家拿来几只食品袋,想为他们采些山楂。他们答应做好果酱与我分享。我们一起动手采摘。我很高兴能够尽一个东道主的友情和礼仪。小徐在片子里特意为我保留了采摘的镜头……。久违的开心时刻又回到我身边。父亲在世时,每逢山楂成熟,总会事先备好一些让我带回市里。如果他老人家九泉有知,定然会为这次采摘感到高兴。
我们采摘了小小的三袋山楂,回到市里。我给于涛留下话,等那女人回来,告诉她我没有办法跟她联系,擅自采取了行动。我心里尚存一点自信,树毕竟是父亲留下的。
过了三天,我得到了来自老家的消息。女人在我走后的第二天回来了。得知我采摘的消息,她没有说什么,面无表情地打开了屋门。是日下午,山楂的浩劫来临了。她挥舞长竿,仍然面无表情地敲落了一树山楂。那些饱满的红艳艳的果实,被乱棒打下,残破不堪,地上一片狼藉。
接到这个消息,我顿感意外,但随之表示理解,心情也平静下来。在没有得到她许可的前提下,我的行动未免冒昧,岂止是冒昧,简直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我让一个老女人肝火上燎,实在是不应该的,但是,说心里话,我没有丝毫的不尊重,更没有丝毫的不妥。我应该有这个权力。
我尽可能为此寻找合理的解释,却怎么也不能忘掉这件事。她完全可以等些日子再采取行动,也应该找人帮忙。树不算太高,但大部分果实需要上到房顶才能够着。一个人把一树山楂敲落是需要体力和时间的。我想不出她怎样独自完成了这件工作。我不明白,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一直接受着我的关照时,为什么竟然会以如此的方式,向一棵树发泄她的满腔怨恨?
父亲的死切断了我与家中的骨肉联系,女人在我回家的路上,密集布下了丛丛荆棘。在这样一条路上行走,需要多大的胆量和勇气……
【山楂落地的消息】相关文章:
2.米颠拜石
3.王羲之临池学书
8.郑板桥轶事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