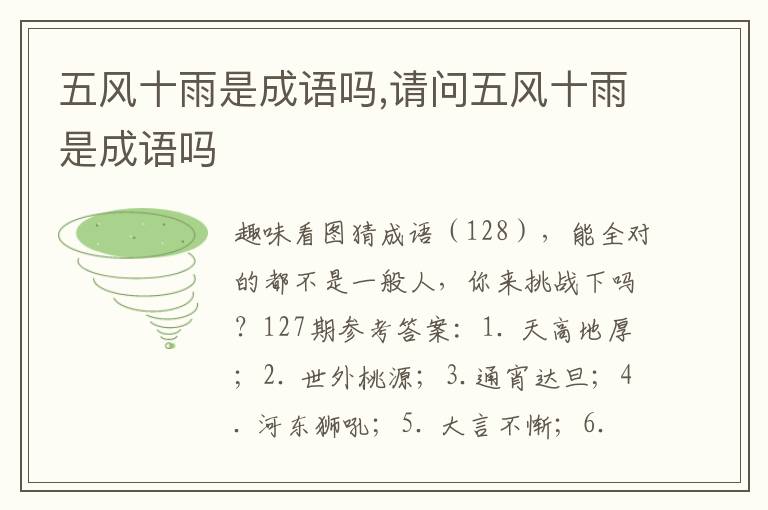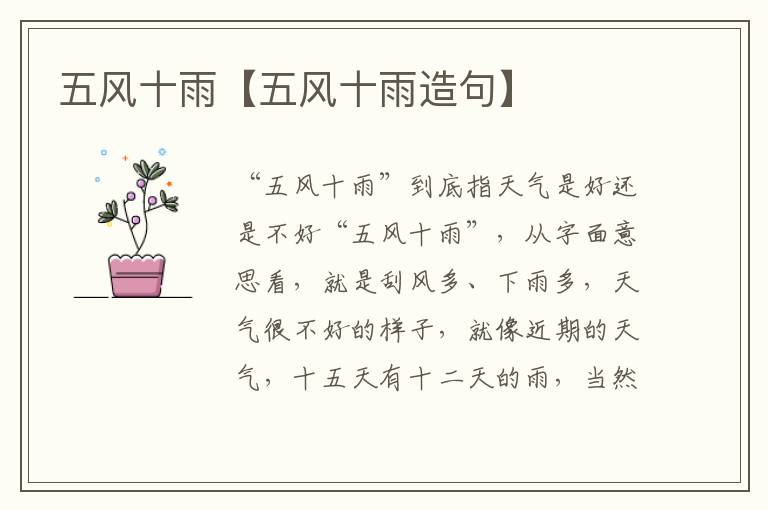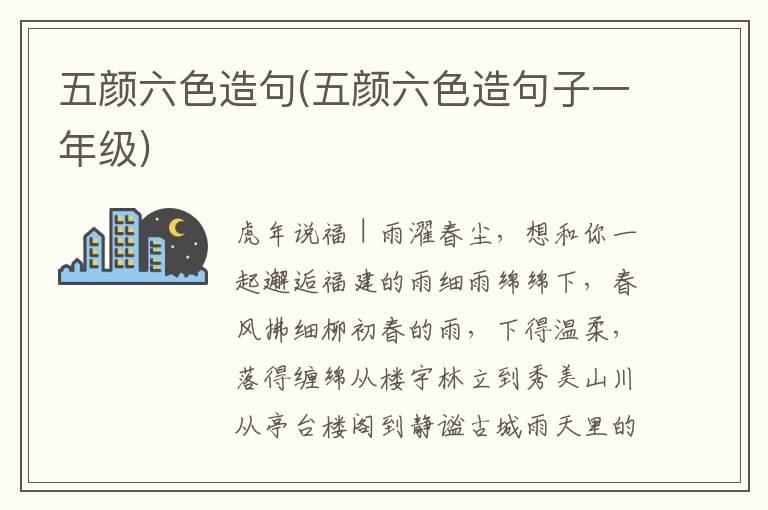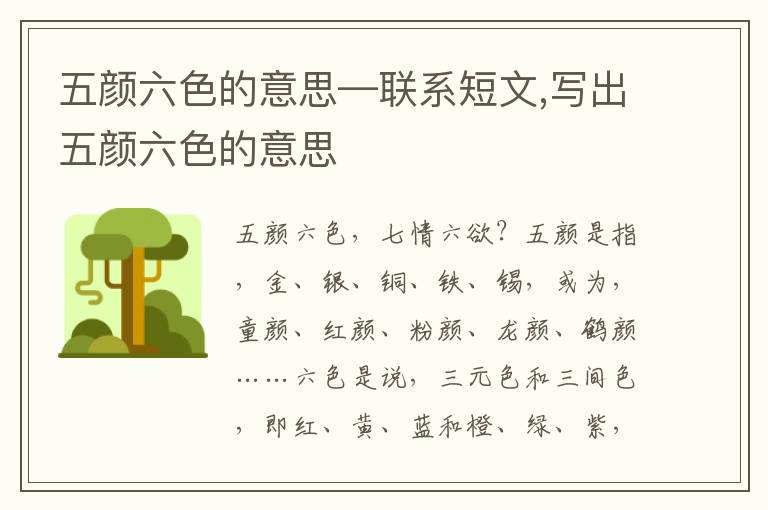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某个夏夜,母亲在地里干完活后,觉得肚子疼痛难忍,但她还是一步一步挪到家里,结果她刚走到卧室门口,便疼倒在地上。最终,她撕心裂肺的叫声唤来了左邻右舍,大家七手八脚地将母亲抬上床,又找来一个据说经验丰富的媒婆,为母亲接生。父亲对于母亲的这一次怀孕,并未太过上心,照例在村头帮人家盖房子,直到天黑下来,才不慌不忙地收拾了东西,准备回家吃母亲做的饭。结果却是遇到母亲难产,生了一天一夜,我才在媒婆连连的哈欠里,呱呱坠地。母亲一看又是一个女孩,自己先自愧疚,休养生息了一个星期,便包了头巾,下地干活。
在我出生的那个月,远在北京的一个女人,提前很长时间便向单位请了产假,在家里静养保胎。在各种营养食品都吃遍之后,我的朋友驰终于在医生手术刀的协助下,降生到锣鼓喧天的尘世。据驰自己讲,因为是家族里的第一个男孩,从爷爷奶奶到外公外婆,无不将他奉为掌上明珠。我在连水果罐头都没有尝过什么味道的时候,驰已经吃腻了凤梨、山楂或者苹果的罐头,也玩够了变形金刚,翻烂了许多本连环画册,又在每天6点半的时候,盯着电视机看黑猫警长。当我在野地里飞奔得满脸脏泥,回家后倒头就睡的时候,驰需要天天洗澡后才能被父母允许上床。我对于玉米麦子高粱大豆有天生的亲切感,而驰则在上大学后出去郊游时,才分清韭菜和麦子的区别。我和小伙伴们天天在相邻的村庄里“暴走”,时不时地会跑上十几里的路,只为看一场外村的露天电影。而为了看一本被人遗忘在墙头上的书,我甚至守在角落里长达3个小时,只等没有人会来取的时候,偷偷地将它带回家去。
那时候我们也会旅游,借了人家的自行车,七八个人浩浩荡荡地开到县城去,有个身材矮小的男孩,很多次都异想天开,要像孙悟空一样,变成一团棉花,钻进袋子里,而后跟着卡车飞到大城市里去。我们曾经在硕大的棉花堆里游玩,也曾对着空旷的粮库高声呐喊。至于那些河流,小的煤矿,军工制衣厂,更是我们乐于探险的风水宝地。而那时的驰,时不时地,就跑到我在课本上才能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上去放风筝,或者坐着父亲的吉普车,威风凛凛地四处兜风。他每天上学,都会乘坐公共汽车,而我,看见老师挂着有巴士的图画,常常会想,为什么父母没有在生下我后,将我送给售票员家里养呢?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坐车去上学了。
而我与驰,就这样在相差巨大的环境里,毫不相干地生长着。我像田间地头的一株草,哪怕被人无情地拔下,只要根上还沾着土,照例又能在阳光下抽枝展叶,生机勃勃。而驰,则是城市里的一栋房子,生来就代表了尊贵和优越。风再猛,雨再大,躲进去,便是温室里的花朵,无须为生计奔波劳碌。
18年后的秋天,我与驰,相遇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我们一前一后地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读书学习。只不过,我为了能够来到北京,需要比驰多考出近100分的分数。我们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我尽力地要向更高更远处奔跑,而驰,却出乎意料地,朝着我来时的方向兴致勃勃地走。我们在北京,结成互助的驴友。他带我游走故宫、长城、三里屯,我则拿着我们小城的地图,告诉他,哪里是我常去的山,哪里是我爱游的水,哪里又有满山的桃花,和无人采摘的野枣。驰答应给我弄免费的明星演唱会的门票,我则保证驰去了我们小城,会有吃不完的野果,看不尽的山水。
我一直以为,让我惶恐无助自觉渺小无依的北京,不会留下我太深的足迹。而它,亦不会多么热情地,将我这个乡下来的丑小鸭用力地挽留。就像儿时去县城的阿姨家,总会被那个自以为是的表妹,毫不留情地抢夺手中的玩具一样,北京,对我的包容,亦是有限度的。但我,并没有在它的冷淡里,赌气,转身走开。我被一种莫名的东西推着,挤着,不由自主地,朝北京的最深处融入。我在毕业的时候,为了能留在北京,与一家毫无保障的私人公司签了约;我一次次频繁地跳槽,试图找到一份最稳定的工作,直到两年后,我发现一切的期望,都化为泡影,除了考研,追寻想象中的稳定与地位,我别无选择。
而这时的驰,与我一样,走走停停,换了许多份工作。只不过,他每一次辞掉工作的原因,都是因为挣的钱足够开始新一轮的“游山玩水”。我曾经问他,难道没有想过,在城市里买一栋房子,安一个温暖的家?驰笑着,说,可是这一切,我父母都早已为我安排好了,我所做的,就是用自己挣来的钱,多出去走走,或许何时累了,就会回父母为我买下的房子里去,不过,现在,还是趁着年轻,多颠簸动荡两年,我可不想为了孩子老婆,早早地就牺牲掉自己的自由。
我一直想,什么时候,我能够走到驰的前面去呢?当我在贫乏的生活里,拼命地想要物质满足的时候,驰早早地便厌倦了一切;当我为了美丽的北京梦,在宿舍昏暗的走廊里深夜苦读的时候,驰却因为出生在北京,可以在10点之前,喝杯新鲜的牛奶,上床休息;当我连电脑的键盘都小心翼翼不敢触摸的时候,驰早已十指飞扬,在网上开设了自己的小店;而当我为了能够真正地打到北京的内部去,在人才市场上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争一碗粥喝的时候,驰却背起了背包,开始我儿时在山水间游走的惬意旅程。
后来的某一天,我在北京的一家外企的办公室里,再次遇到了驰。我们彼此笑笑,说,你好。而后,我坐在办公桌后面,微笑着问驰,为何要来我们公司应聘?驰说,东游西逛了这么多年,我想我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活我的家,我,不能依靠父母一辈子,而父母为我准备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的。
就是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和驰,其实一直坐在同一辆车里,只不过,驰坐在能够看得见风景的位置上,而我,却是在晦暗的角落里。而今,命运终于将我们的位置重新调换;我可以看得见北京的天空和天空中自由飞翔的白鸽,而驰,则在逼仄的角落里,看清了自己昔日的位置。
而那游走在城市与乡村路口处的命运,它原来一直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走到有风景的窗口要多远】相关文章:
2.米颠拜石
3.王羲之临池学书
8.郑板桥轶事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