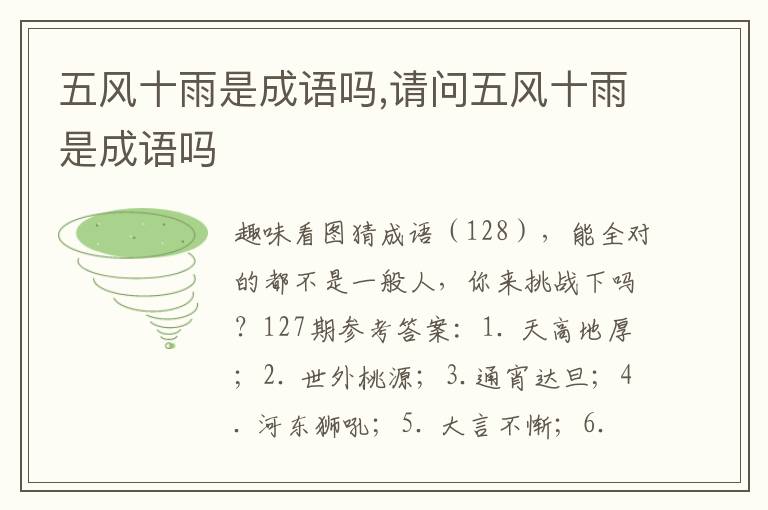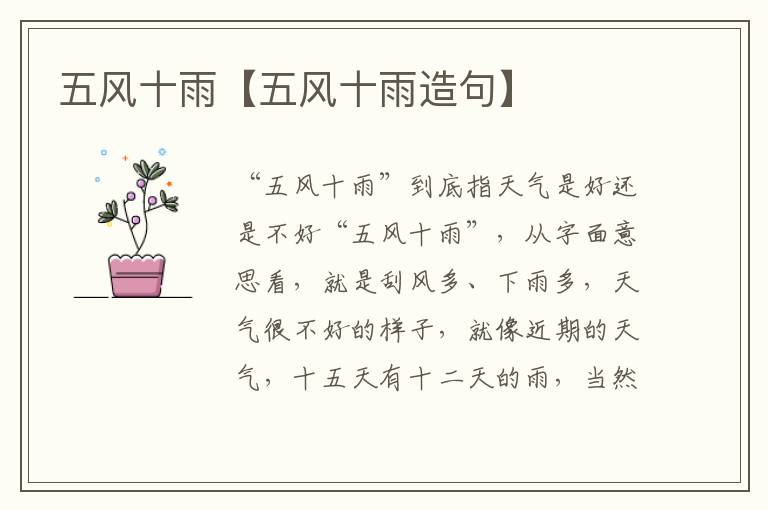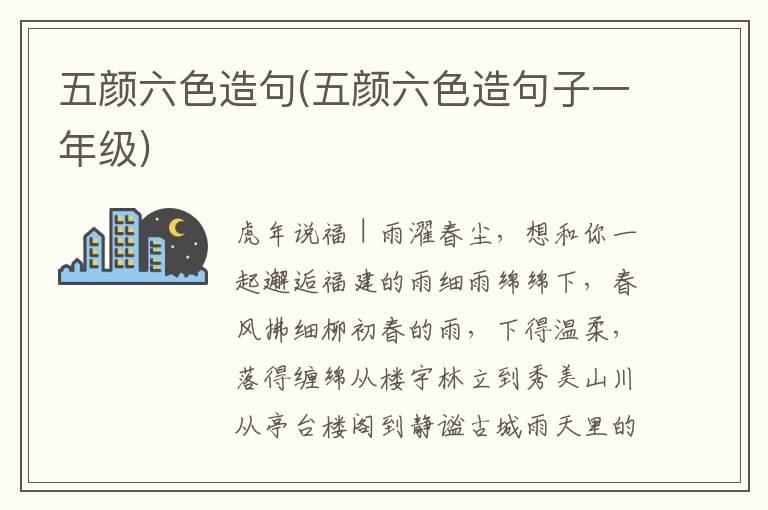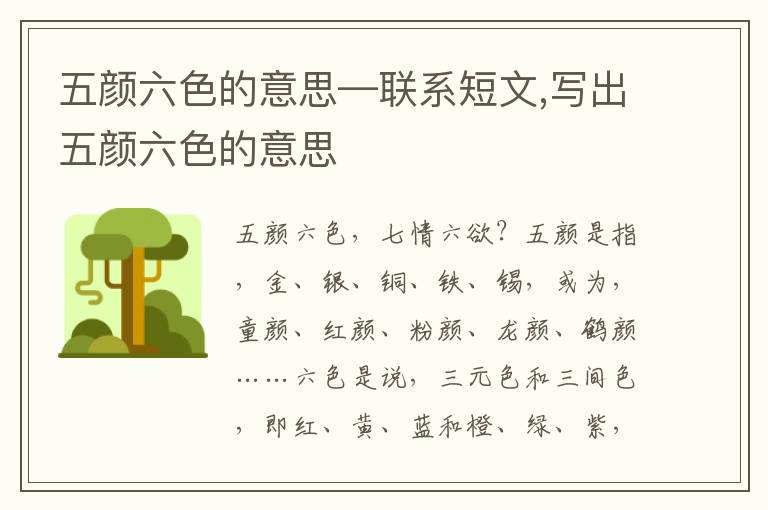到目前为止,我听过的两句让我瞬间掉泪的话,是同一个人说的。这个人是我的死党Y。我对Y的第一印象极好,现在再想,恐怕这种“一见钟情”有两个很具体的原因。
一是Y为人好,初次见面时跟我握了手,且匆忙地扯掉了手套。你要知道,我们那时只有15岁,真诚而美好的人在这个小镇是不多见的。
二是Y眼里的光。那是只有那些被称作理想主义者的人眼里才有的光,笃定而无畏。一看到这道光,我就像在人声鼎沸的他乡一眼认出了同类。
认识Y之后,我终于能够毫无愧疚地畅谈那个小镇的多数人从来都不在意也听不进去的,关于梦想的话题了。Y最大的梦想是漂洋过海去日本。他对日本动漫近乎痴狂,尤其喜欢日本动画导演新海诚。虽然他常自嘲和新海诚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很宅”,但我知道他胸中的天空绝对像新海诚笔下的一样壮阔。
因此,Y上大学并没有选择动画专业,而是选择了日语,为去日本生活做准备。相比之下,我的理想就相形见绌了,我想去的地方是坐火车就能直达的北京。
上大学之后,虽然我跟Y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通话的时间,甚至超过了跟父母软磨硬泡讨生活费的时间。
只有刚上大二那阵联系比较少,那时Y交了女朋友,还以此为理由跟我借了几次钱。不过,他俩没过多久就分手了。Y最后一次跟我聊未来,是在我们刚上大三那会儿。
Y连夜坐火车来北京跟我聊天,因为前一晚我给他打电话说自己想退学,所以当我看到他站在我宿舍门口,直接被吓傻了。Y问我见到他高不高兴,我說高兴。Y又问我可知道他为啥来北京,我说不知道。Y笑了笑,说,我就是想用实际行动支持你。
我从未在Y眼里看到那么亮的光。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不是光,而是即将涌出又忍回去的眼泪。
那时我才知道了Y在大二那年并没有交女朋友,向我借钱是因为:他们日语系那年有两个到大阪的交换生名额。Y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
Y在选择日语专业时曾跟父亲大吵一架。最终,他瞒着所有人,申请且拿到了名额,并从一位前辈那里联系到大阪一家专门招收外国留学生兼职的温泉浴场。前辈提醒他工作会很辛苦,经常要忙到凌晨4点,但这些,Y怎么会介意呢?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辛苦是最容易克服的障碍。
唯一令Y苦恼的是前期费用,因此他开始借“女朋友”的名义在我们这群好友里四处“行骗”。
Y是在机场被他父亲抓住的。出发当天,Y终究因为不舍,给母亲打了电话,却被母亲听出他声音里的异样,以及车站里回荡的广播声。
很快,他父亲在他检票的前一秒赶到,一把抓住往进站口逃窜的Y,把他带了回去。
两年后,Y考上了公务员。上班之前,Y又来北京找了我一趟。那天Y很开心,喝了很多酒,我却发现他眼里十多年的光就这么没了。
Y的第一句让我瞬间掉泪的话,就是这时候说出口的。他说,对不起啊,小北,不能陪你了,我的梦想只能陨落了。
我一听到这句话,眼泪立刻就下来了,脑袋里突然就出现一颗即将陨落的星辰。这颗星辰明亮巨大,却抵不住大地的牵引力,拖着长长的如挽歌一般的火焰,在落地前的最后一秒燃烧殆尽。
Y知道用不了两年,他将混入曾经最不想成为的那一类人当中。他说他要练习不去想起新海诚,因为那片天空已经开始让他隐隐作痛。
我们都已是成年人了,或多或少经历了一些事,懂得一些道理,可为什么还是有大多数人的生活依旧是迷茫、庸碌、粗糙?大概是缺乏决定需要的勇气、担当。我们也没有必要为现有的过不好,而找其他借口,为自己做一个可笑的交代。
Y的第二句让我瞬间掉泪的话,是去年过年时跟我说的。一天,我在他家阳台的角落里发现堆着好多大小不一的木板。我问Y那些是什么,Y慌忙跑过来,一边红着脸狡辩,一边在我与木板之间徒劳地挡住我的视线。
那些木板上,画着各式各样的天空。这是Y这几年每天从单位下班后悄悄画下的天空。每片天空下都有一个相同的签名,这个签名我似乎在哪里见过。
我说你该不会出画集了吧?Y终于不再害羞和扭捏,笑着说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打开电脑,点开某个日本动漫的视频,在播放到十多秒的时候,他的名字出现了——××日语字幕翻译组组长。
我笑了很久,眼泪都笑出来了,我说原来这个人是你啊,原来我看的字幕是你做的。
Y又恢复了之前的扭捏,说他其实只是打发时间而已。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说,其实还是放不下,就当练习日语了,万一以后能用到呢?说完,Y开始哈哈大笑,眼里又闪起那道我多年都未见到的光。
回家路上,Y给我发来一条信息,是一句日语:“一緒にきらきらになりましょう。”我用翻译软件一查,眼泪立刻止不住了——“我回来了,希望小北君不要嫌弃呀。”
在我完成了一次次的命运迁徙后,我发现了一个让人欣慰的事实: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很多星辰在不断陨落着,但还有很多星辰在千方百计地升起。
愿我们都是不落的星辰,愿你我永不落单。
【愿我们都是不落的星辰】相关文章:
2.米颠拜石
3.王羲之临池学书
8.郑板桥轶事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