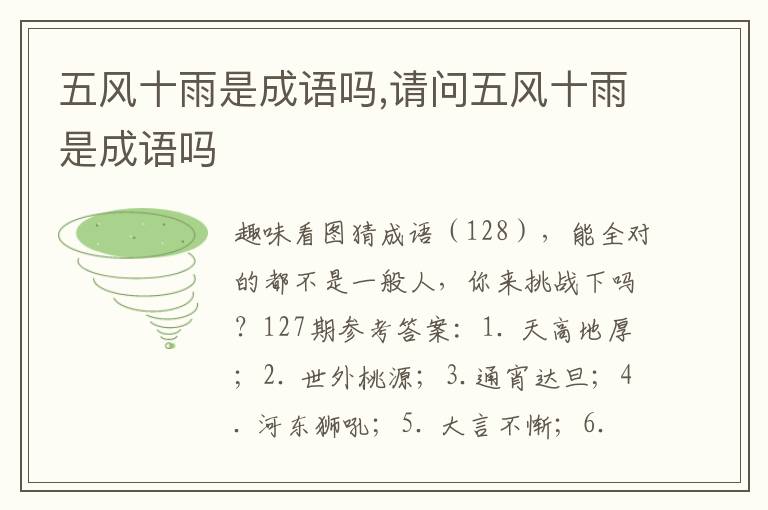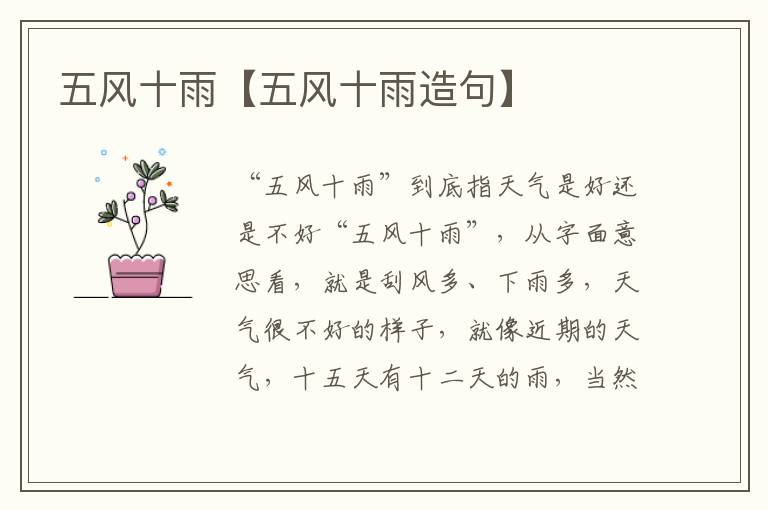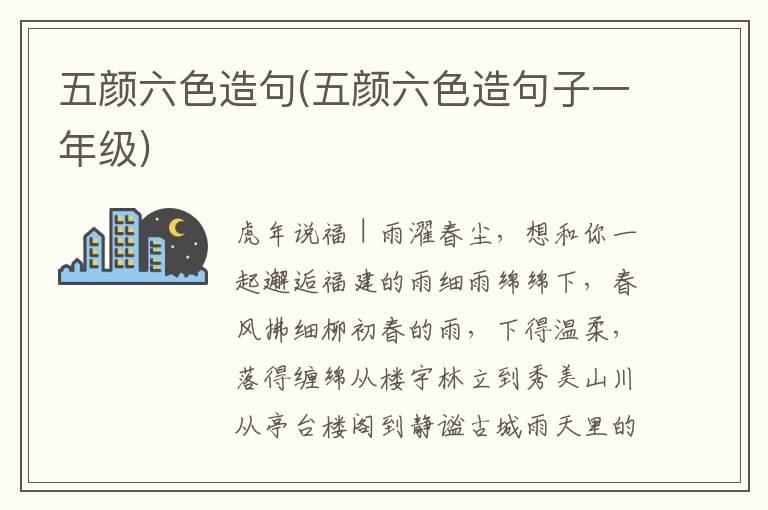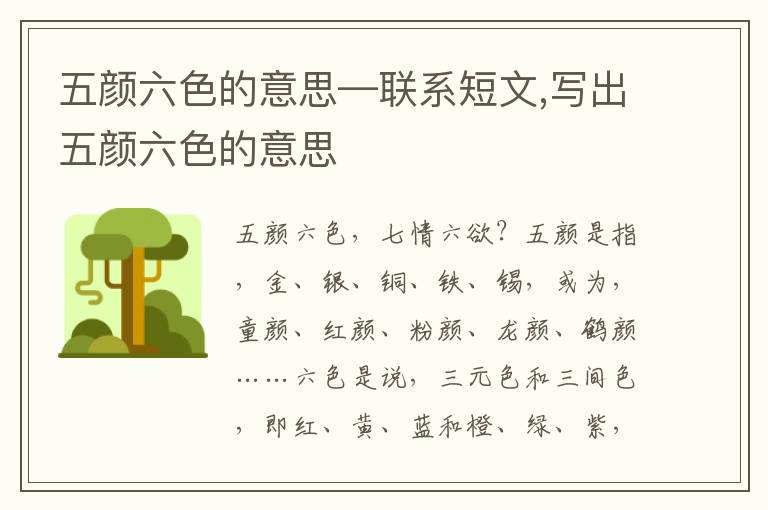至少有75位演员曾经饰演过福尔摩斯,让他成为电影电视史上最常出现的人物。伊恩·麦克莱恩即将成为最新的一位,扮演1947年的老年福尔摩斯。BBc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出演的《福尔摩斯》第三季刚刚上映,传言小罗伯特·唐尼可能还会出演一次福尔摩斯电影。
我们对卷福的热爱似乎永无止境。但为什么?表面看来,福尔摩斯不太像是一个英雄。他不体贴,自大,脾气坏,从来没有爱情,讨厌社交。
他更像一名科学家。他的个性是我们对科学家的一切典型印象的大集合——独居,内向,大胆,无所顾忌,略微不讲人性,残酷,执着,有想象力,聪明。
福尔摩斯诞生的那个世界,是一个迷恋科学的世界。维多利亚时代见证了查尔斯·巴贝奇的“计算机器”的诞生,它是现代电脑的先驱。许多早期的虚构侦探——爱伦·坡的杜平,贾克·福翠尔的“思考机”——都是擅长条分缕析不带感情分析谜团且引以为傲的人物。
福尔摩斯也曾夸耀自己的缺乏感情——“我是个大脑,华生。剩下的都是附件而已。”
还有他的将事实和理论分离的能力。“我一直注意,从不带任何偏见,”他在《瑞盖特村之谜》中对警探佛瑞斯特说,“我只是恭顺地让事实引领我前行。”正如巴贝奇的差分机,其中没有人格参与,只有方法的应用。“他是,”“全世界最完美的推论和观察机器。”华生说。
但是柯南·道尔也知道,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哪怕是通俗文学虚构人物,能仅靠冰冷的、机械的逻辑生存。按部就班没有想象力的事实收集者——柯南·道尔很不厚道地用全部职业警察局来代表——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科学家的典型形象。福尔摩斯也是一个避世的、怪僻的波西米亚人(另类生活方式的追求者),同样也会依赖直觉和神秘的灵光一现。
在《红发会》里,他在调查途中暂停下来前往“提琴地”,在那里他“坐在小凳上,浑身散发着最完美的快乐,随着音乐的节拍轻柔地挥动细长的手指”。他解决了《歪嘴的人》的谜团,靠的是整晚坐在一堆枕头上,枕头堆成某种“东方的神明”,抽着烟,“眼睛空洞地盯着天花板的角落”。
其他时候,他会完全放弃脑力方法,选择老套的拳斗。“接下来几分钟非常刺激,”他在《独行骑者疑案》里对华生说,“一记左直拳正打在那个恶棍身上。”其他一些时候,他说自己是“穿皮靴子的人里最无可救药的懒鬼”。
把这些看似矛盾的特征集合起来,我们的福尔摩斯成为了比他所有虚构对手都更真实的科学家、更真实的人。
正如福尔摩斯在《血字的研究》里说的,“无色的生命线团之中,有猩紅的谋杀丝线穿梭。而我们的目的就是解开线团,找到丝线,探索它的每一寸角落”。
这,也许就是我们之所以迷恋福尔摩斯、迷恋科学的核心。我们因这个想法而感到安心:不管谜题有多么令人困惑,总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总有一个人能找到它。福尔摩斯仅用逻辑、想象力和偶尔派出街边小孩就能解决问题,而不需要难以置信的仪器或者超能力,这种念头令人宽慰。但是我们对卷福的爱,和科学一样,也是有所担忧的。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为了追求真相愿意走多远。
【其实,福尔摩斯是个科学家】相关文章:
2.米颠拜石
3.王羲之临池学书
8.郑板桥轶事十则